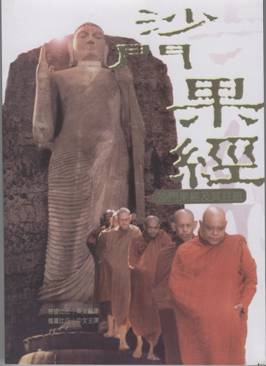Ⅰ. 經文篇
沙門果經
(Sāmaññaphala Sutta)
回首頁
群臣之言
1.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王舍城(Rājagaha)耆婆王子育(Jīvaka Komārabhacca)的芒果園,與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眾在一起。那時,正值十五日布薩,乃是第四個月拘物提的月圓之夜。摩羯陀國韋提希王后之子阿闍世王(King Ajātasattu)在群臣圍繞之下,正坐在皇宮上層的陽台。那時阿闍世王發出如此的歡喜讚歎:
「諸位賢友,這是多麼宜人的月夜啊!這是多麼美麗的月夜啊!這是多麼可愛的月夜啊!這是多麼寧靜的月夜啊!這是多麼吉祥的月夜啊!今晚,是否有那一位沙門或婆羅門,能在我們去拜訪之後帶給我內心安寧?」
2. 這時,有一個大臣說:「陛下,布蘭迦葉(Pūraṇa Kassapa)是一方教團之首、群眾之首、群眾之師、聲名顯赫、是眾人尊為神聖的精神領袖。他高齡、出家已久、年長、已達到生命的後期。陛下應當拜訪他;他或許能帶給您內心安寧。」然而,當他如此稟告時,阿闍世王只是沉默不語。
3-7. 其他的大臣稟告說:「陛下,末伽梨瞿舍梨(Makkali Gosāla)……阿耆多翅舍欽婆羅(Ajita
Kesakambala)……波拘陀迦旃延(Pakudha
Kaccāyana)……薩若毘耶梨弗(Sañjaya
Belaṭṭhaputta)……尼乾陀若提子(Nigaṇṭha
Nāṭaputta)是教團之首、群眾之首、群眾之師、聲名顯赫、是眾人尊為神聖的精神領袖。他高齡、老邁、年長、耆宿。陛下應當拜訪他;他或許能帶給您內心安寧。」然而,當他如此稟告時,阿闍世王只是沉默不語。
8. 這時,耆婆王子育正沉默地坐在距離阿闍世王不遠之處。於是阿闍世王問他說:「賢友耆婆,你為什麼保持沉默?」
耆婆稟告說:「陛下,世尊、阿羅漢、圓滿覺悟者與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眾正住在我們的芒果園。關於世尊,如此的善名遍傳各處:『世尊是阿羅漢、圓滿覺悟者、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陀、世尊。』陛下應當拜訪世尊。陛下若拜訪他,或許他能帶給陛下內心安寧。」
9. 「那麼就將象乘準備妥當吧!賢友耆婆。」耆婆回答說:「遵命!陛下。」於是耆婆準備了五百隻雌象,以及國王御用的雄象。然後稟報國王說:「陛下,象乘已備妥,聽候您的吩咐。」
10. 阿闍世王就命令他的五百位王妃乘坐雌象,一人乘坐一隻,而他本人則乘坐御用的雄象。在他的隨從們各執持火炬的擁護下,皇威顯赫地從王舍城出發,朝向耆婆的芒果園而去。
到了距離芒果園不遠的地方,阿闍世王突然被恐怖、疑懼與驚駭所籠罩,基於害怕、焦慮及被怖畏所侵襲,他問耆婆說:「你不是在欺騙我吧,賢友耆婆?你不是在出賣我,要使我落入敵人的手中吧?若真有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住在這裏,怎麼可能完全寂然無聲,連一點噴嚏或咳嗽的聲音都沒有?」
「不要害怕,大王,不要害怕。陛下,我並沒有欺騙您、出賣您或使您落入敵人的手中。向前走,大王,向前走!那些正是點燃在會堂中的燈火。」
沙門果之問
11. 阿闍世王騎坐象乘直到象乘所能達到的盡頭,然後從象乘上下來,步行到會堂門口。到了門口,他問耆婆說:「耆婆,世尊在那裡?」
「那位就是世尊,大王,就是坐在比丘眾之前、背向中柱、面向東方的那一位。」
12. 於是阿闍世王走近世尊,站立在一旁。當他站在那裡,環視如一片寧靜湖水般安詳默然坐著的眾比丘,他發出如此的歡喜讚歎:「願我的兒子優陀夷跋陀王子也能享有這些比丘現在享有的安寧!」
(世尊說:)「大王,你的意念是否聽從情感的感召?」
「尊者,我愛我的兒子優陀夷跋陀王子,願他能享有這些比丘現在享有的安寧。」
13. 於是阿闍世王禮敬世尊,虔誠地向比丘眾致敬,坐在一旁,然後對世尊說:「尊者,我想請問世尊一件事,可否撥空為我解答?」
「儘管問吧,大王。」
14. 「尊者,世間有各種行業,如:馴象師、馴馬師、馬車夫、弓術家、搬運工、兵營將官、突擊兵、皇家重臣、前線軍、騎牛軍、軍隊勇士、鎧甲兵、家奴、糖果商、理髮師、侍浴者、廚師、製花環者、洗衣工、織工、編籃者、陶藝家、統計學家、會計師及類似性質的其他行業。所有這些人都享有他們行業當下可見的成果:他們本身得到快樂與歡喜,並且將快樂與歡喜帶給他們的父母、妻兒、朋友及同事;他們對沙門與婆羅門所作出的殊勝供養能導向善趣、結成樂報、引生天界。尊者,可否指出同樣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15. 「大王,你是否記得曾經問過其他沙門與婆羅門這個問題?」
「我記得曾經問過他們,尊者。」
「如果你不覺得麻煩的話,請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回答的。」
「尊者,當有世尊或與世尊同樣的人在場時,我不覺得麻煩。」
「那麼就說吧,大王。」
布蘭迦葉的教理 回首頁
16. 「有一次,我去見布蘭迦葉。互相寒暄與問安之後,我坐在一旁,請問他說:(與第14節相同的話),他是否能指出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17. 當我說完之後,布蘭迦葉對我說:『大王,如果有人自己做,或指使別人做;自己切斷他人手腳,或指使別人切斷他人手腳;自己折磨他人,或指使別人折磨他人;自己使他人遭受悲痛,或指使別人使他人遭受悲痛;自己壓迫他人,或指使別人壓迫他人;自己威嚇他人,或指使別人威嚇他人;如果他殺生、偷盜、闖入人宅、劫奪財物、竊盜、攔路搶劫、通姦、說謊──他並沒有造下罪惡。如果有人用邊緣鋒利的圓盤將大地所有眾生切成一整堆的肉塊,這樣做既沒有罪惡,也沒有罪惡的果報。如果有人沿著恆河南岸殺生,或指使別人殺生;斷人手足,或指使別人斷人手足;施加酷刑,或指使別人施加酷刑,如此做既沒有罪惡,也沒有罪惡的果報。如果有人沿著恆河北岸行布施,或指使別人行布施;做供養,或指使別人做供養,如此做既沒有善業,也沒有善業的果報。奉行布施、自制、持戒及說誠實語既沒有善業,也沒有善業的果報。』
如是,尊者,當我請問布蘭迦葉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解釋造業無效(的教理)給我聽。尊者,就像有人被問到芒果時,卻談論有關麵包果的事;或者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談論有關芒果的事。同樣地,當我請問布蘭迦葉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解釋造業無效(的教理)給我聽。尊者,那時我心裡想:『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想要刁難活在他自己領土的沙門或婆羅門。』因此,我對布蘭迦葉的話既不隨喜,也不反駁。然而,儘管既不隨喜也不反駁他的話,我卻仍然感到不滿意,但是一句不滿意的話也沒說。我沒有接受、沒有信奉他的教理,就從座位上起身、離去。
末伽梨瞿舍梨的教理 回首頁
18. 尊者,又有一次,我去見末伽梨瞿舍梨。互相寒暄與問安之後,我坐在一旁,請問他說:(與第14節相同的話),他是否能指出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19. 當我說完之後,末伽梨瞿舍梨對我說:『大王,眾生的煩惱沒有因或緣;不具備任何因緣,眾生就生起煩惱。眾生的淨化沒有因或緣;不具備任何因緣,眾生就得以淨化。沒有自決定、沒有他決定、也沒有個人決定。沒有能力、沒有活力、沒有個人力量、也沒有個人剛毅。一切有情、一切眾生、一切生物、一切靈魂都是無助、無力、無能的。他們透過命運、環境與本質而進行轉變,在六類人當中經歷苦樂。
(眾生)有一百四十萬種主要的生起形式、六千種(其他形式)及六百種(其他形式)。有五百種業、五種業、三種業、滿業及半業。有六十二道、六十二小劫、六類人、八個人生階段、四千九百種謀生法、四千九百種修行人、四千九百種龍宅、二千根、三千地獄、三十六塵界、七個有想有情界、七個無想有情界、七種節生植物、七種神、七種人、七種阿修羅、七大湖、七種主要的結、七百種次要的結、七種主要的絕壁、七百種次要的絕壁、七種主要的夢、七百種次要的夢、八百四十萬大劫。愚者與智者在這些當中流轉之後,就會同樣地達到苦的止息。
雖然有人會想:「藉著道德修養、或持戒、或頭陀行、或梵行,我將能使未成熟的業成熟,以及去除已成熟而現起的業。」──那是不可能的,因為苦樂都是早已決定。輪迴的界限是固定的,既不能縮短,也不能延長;既沒有前進,也沒有後退。就好像一粒線團被拋擲出去時,它會鬆開地滾下去,直到線的盡頭為止;同樣地,愚者與智者流轉(固定的期限),然後他們都達到苦的息滅。』
20. 如是,尊者,當我請問末伽梨瞿舍梨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解釋透過在輪迴中流轉而淨化(的教理)給我聽。尊者,就像有人被問到芒果時,卻談論有關麵包果的事;或者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談論有關芒果的事。同樣地,當我請問末伽梨瞿舍梨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解釋透過在輪迴中流轉而淨化(的教理)給我聽。尊者,那時我心裡想:『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想要刁難活在他自己領土的沙門或婆羅門。』因此,我對末伽梨瞿舍梨的話既不隨喜,也不反駁。然而,儘管既不隨喜也不反駁他的話,我卻仍然感到不滿意,但是一句不滿意的話也沒說。我沒有接受、沒有信奉他的教理,就從座位上起身、離去。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的教理 回首頁
21. 尊者,又有一次,我去見阿耆多翅舍欽婆羅。互相寒暄與問安之後,我坐在一旁,請問他說:(與第14節相同的話),他是否能指出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22. 當我說完之後,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對我說:『大王,沒有布施、沒有供養、沒有解脫。沒有善惡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來生、沒有父親、沒有母親、沒有投生的眾生。在這個世間上,沒有能以其親身現知與領悟來解釋今生及來生的正證正行沙門與婆羅門。人由四大組成,死時,(他身體中的)地回歸及併入(外在的)地體;(他身體中的)水回歸及併入(外在的)水體;(他身體中的)火回歸及併入(外在的)火體;(他身體中的)風回歸及併入(外在的)風體;他的感官歸於虛空;四個人以棺架抬著他的屍體,對他的讚頌被唱誦到墳場為止,他的骨頭轉變成鴿子色,他的慈善布施終歸於灰燼。布施是愚人的教理。宣示有(來生)的人只是在講虛假空話。身體分解之後,愚者與智者同樣地滅絕與完全消失,他們死後不再存在。』
23. 如是,尊者,當我請問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解釋斷滅(的教理)給我聽。尊者,就像有人被問到芒果時,卻談論有關麵包果的事;或者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談論有關芒果的事。同樣地,當我請問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解釋斷滅(的教理)給我聽。尊者,那時我心裡想:『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想要刁難活在他自己領土的沙門或婆羅門。』因此,我對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的話既不隨喜,也不反駁。然而,儘管既不隨喜也不反駁他的話,我卻仍然感到不滿意,但是一句不滿意的話也沒說。我沒有接受、沒有信奉他的教理,就從座位上起身、離去。
波拘陀迦旃延的教理 回首頁
24. 尊者,又有一次,我去見末波拘陀迦旃延。互相寒暄與問安之後,我坐在一旁,請問他說:(與第14節相同的話),他是否能指出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25. 當我說完之後,末波拘陀迦旃延對我說:『大王,有七身是未經製作、未經形成、未經創造的、沒有創造者、不生、穩定如山峰、堅立如柱的。它們不變化、不更改、不互相障礙。它們不能造成彼此苦、或樂、或苦樂。是那七身呢?地身、水身、火身、風身、樂、苦及靈魂為第七身。在這些當中,沒有殺生者,也沒有令別人殺生者;沒有聽聞者,也沒有令別人聽聞者;沒有認知者,也沒有令別人認知者。若有人以利劍砍掉(別人的)頭,他並沒有殺害(別人的)生命,利劍只是通過七身之中的空間而已。』
26. 如是,尊者,當我請問末波拘陀迦旃延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以完全不相關的話回答我。尊者,就像有人被問到芒果時,卻談論有關麵包果的事;或者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談論有關芒果的事。同樣地,當我請問末波拘陀迦旃延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以完全不相關的話回答我。尊者,那時我心裡想:『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想要刁難活在他自己領土的沙門或婆羅門。』因此,我對末波拘陀迦旃延的話既不隨喜,也不反駁。然而,儘管既不隨喜也不反駁他的話,我卻仍然感到不滿意,但是一句不滿意的話也沒說。我沒有接受、沒有信奉他的教理,就從座位上起身、離去。
尼乾陀若提子的教理 回首頁
27. 尊者,又有一次,我去見尼乾陀若提子。互相寒暄與問安之後,我坐在一旁,請問他說:(與第14節相同的話),他是否能指出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28. 當我說完之後,尼乾陀若提子對我說:『大王,尼乾陀教徒是無結者,受四重戒的約束。何以如此?在此,大王,尼乾陀教徒禁絕涉及一切水;他天生免離一切罪惡;他透過免離一切罪惡而淨化;他充滿免離一切罪惡。大王,當尼乾陀教徒受到這四重戒約束時,他被稱為自圓、自制、自立的無結者。』
29. 如是,尊者,當我請問尼乾陀若提子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向我解釋四重戒。尊者,就像有人被問到芒果時,卻談論有關麵包果的事;或者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談論有關芒果的事。同樣地,當我請問尼乾陀若提子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向我解釋四重戒。尊者,那時我心裡想:『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想要刁難活在他自己領土的沙門或婆羅門。』因此,我對尼乾陀若提子的話既不隨喜,也不反駁。然而,儘管既不隨喜也不反駁他的話,我卻仍然感到不滿意,但是一句不滿意的話也沒說。我沒有接受、沒有信奉他的教理,就從座位上起身、離去。
薩若毘耶梨弗的教理 回首頁
30. 尊者,又有一次,我去見薩若毘耶梨弗。互相寒暄與問安之後,我坐在一旁,請問他說:(與第14節相同的話),他是否能指出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31. 當我說完之後,薩若毘耶梨弗對我說:『如果你問我:
甲、1. 「是否有來世?」若我認為有來世,我會告訴你:「有來世。」但是我並不說:「是這樣。」也不說:「是那樣。」也不說:「是別樣。」我不說:「不是如此。」也不說:「非不是如此。」
同樣地,你可能會問我下列的問題:
甲、2. 「是否沒有來世?」
3. 「是否既有來世,又沒有來世?」
4. 「是否既非有來世,也非沒有來世?」
乙、1. 「是否有眾生再投生?」
2. 「是否沒有眾生再投生?」
3. 「是否既有眾生再投生,又沒有眾生再投生?」
4. 「是否既非有眾生再投生,也非沒有眾生再投生?」
丙、1. 「是否有善惡業的果報?」
2. 「是否沒有善惡業的果報?」
3. 「是否既有善惡業的果報,又沒有善惡業的果報?」
4. 「是否既非有善惡業的果報,也非沒有善惡業的果報?」
丁、1. 「如來死後是否還存在?」
2. 「如來死後是否不存在?」
3. 「如來死後是否既存在,又不存在?」
4. 「如來死後是否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若我認為是如此,我會告訴你「是如此。」但是我不說:「是這樣。」也不說:「是那樣。」也不說:「是別樣。」我不說:「不是如此。」也不說:「非不是如此。」』
32. 如是,尊者,當我請問薩若毘耶梨弗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推諉地回答。尊者,就像有人被問到芒果時,卻談論有關麵包果的事;或者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談論有關芒果的事。同樣地,當我請問薩若毘耶梨弗可見的沙門果時,他卻推諉地回答。尊者,那時我心裡想:『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想要刁難活在他自己領土的沙門或婆羅門。』因此,我對薩若毘耶梨弗的話既不隨喜,也不反駁。然而,儘管既不隨喜也不反駁他的話,我卻仍然感到不滿意,但是一句不滿意的話也沒說。我沒有接受、沒有信奉他的教理,就從座位上起身、離去。
第一種可見的沙門果 回首頁
33. 如此,尊者,我請問世尊:尊者,世間有各種行業,如:馴象師、馴馬師、馬車夫、弓術家、搬運工、兵營將官、突擊兵、皇家重臣、前線軍、騎牛軍、軍隊勇士、鎧甲兵、家奴、糖果商、理髮師、侍浴者、廚師、製花環者、洗衣工、織工、編籃者、陶藝家、統計學家、會計師、以及類似性質的其他行業,(從事這些行業的)所有這些人都享有他們行業當下可見的成果:他們本身得到快樂與歡喜,並且將快樂與歡喜帶給他們的父母、妻兒、朋友及同事;他們以殊勝的禮物供養給沙門與婆羅門──導向善趣、結成樂報、引生天界。尊者,可否指出同樣當下可見的沙門成果?」
34. 「可以,大王。且讓我問你這件事,照著你認為適當的情況回答我。
你認為如何,大王?假設你有一個奴隸,他是一個工人,比你早起、比你晚睡、做你想做之事、總是為了你的快樂而行、對你說話客氣有禮、始終留意你是否滿意。他心中可能會如此想:『善行的果報實在太美好、太殊妙了!此阿闍世王是人,我也是人;然而阿闍世王就像天神一般,充分地享受五欲之樂,而我只是他的奴隸、他的工人──比他早起、比他晚睡、做他想做之事、總是為了他的快樂而行、對他說話客氣有禮、始終留意他是否滿意。如果我行善的話,我也能像他一樣。且讓我剃除鬚髮,穿著橘黃色袈裟,離開在家生活出家去吧。』
過了一段時間,他剃除鬚髮,穿著橘黃色袈裟,離開在家生活而出家。出家之後,他於身、口、意方面自制地安住,滿足於最簡單的飲食與住所,樂於獨住。假使你的部下將這一切情況報告給你,你是否會說:『來人!將那個人帶回來,叫他再作我的奴隸、我的工人,比我早起、比我晚睡、做我想做之事、總是為了我的快樂而行、對我說話客氣有禮、始終留意我是否滿意。』?」
35. 「當然不會,尊者。相反地,我會禮敬他,尊重地起立迎接他,邀請他坐,請他接受我供養的袈裟、缽食、住所及醫藥。並且我會提供他正當的保護、防衛與安全。」
36. 「你認為如何,大王?若是如此,是否有可見的沙門果?」
「當然有,尊者。」
「大王,這就是我要為你指出的第一種當下可見的沙門果。」
第二種可見的沙門果
37. 「尊者,可否指出其他當下可見的沙門果?」
「可以,大王。且讓我問你這件事,照著你認為適當的情況問答我。
你認為如何,大王?假設有一個農夫,他是一個平民,納稅以維持皇家的收入。他心中可能會如此想:『善行的果報實在太美好、太殊妙了!此阿闍世王是人,我也是人;然而阿闍世王就像天神一般,充分地享受五欲之樂,而我只是一個農夫,一個平民,納稅以維持皇家的收入。如果我行善的話,我也能像他一樣。且讓我剃除鬚髮,穿著橘黃色袈裟,離開在家生活出家去吧。』
過了一段時間,他捨棄財產,不論財產多或少;捨棄親族,不論親族大或小;剃除鬚髮,穿著橘黃色袈裟,離開在家生活而出家。出家之後,他於身、口、意方面自制地安住,滿足於最簡單的飲食與住所,樂於獨住。假使你的部下將這一切情況報告給你,你是否會說:『來人!將那個人帶回來,叫他再作農夫、平民,納稅以維持皇家的收入。』?」
38. 「當然不會,尊者。相反地,我會禮敬他,尊重地起立迎接他,邀請他坐,請他接受我供養的袈裟、缽食、住所、醫藥。並且我會提供他正當的保護、防衛與安全。」
39. 「你認為如何,大王?若是如此,是否有可見的沙門果?」
「當然有,尊者。」
「大王,這就是我要為你指出的第二種當下可見的沙門果。」
更殊勝的沙門果
40. 「尊者,可否指出比這兩種更殊勝與崇高的其他種當下可見的沙門果?」
「可以,大王,諦聽及注意,我將為你說。」
阿闍世王回答世尊說:「是的,尊者。」
41. 世尊說:「在此,大王,如來出現於世間,他是阿羅漢、圓滿覺悟者、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陀、世尊。他以親身現證的智慧明瞭這個有諸天、諸魔、諸梵天的世間,這個有諸沙門與婆羅門、諸王與人的世代,他廣令眾知。他說法初善、中善、後善,具足義理與辭句。他顯示徹底圓滿與清淨的梵行。
42. 平民、或平民之子、或生於其他種姓的人來聽聞佛法。聞法之後,他對如來生起信心。具備信心之後,他思惟:『在家生活是擁擠的、是塵擾之途;出家則有如曠野一般開闊。在家人不容易過著徹底圓滿、徹底清淨、如磨亮的螺貝那般光明的梵行生活。且讓我剃除鬚髮,穿著橘黃色袈裟,離開在家生活出家去吧。』
43. 過了一段時間,他捨棄財產,不論財產多或少;捨棄親族,不論親族大或小;剃除鬚髮,穿著橘黃色袈裟,離開在家生活而出家。
44. 出家之後,他遵守波提木叉戒,具足正當的行為與行處。自從受戒之後,就依戒自律,見到最小的過失也能帶來的危險。他擁有良好的身語業,活命清淨,具足戒行。他守護六根之門,具足正念與正知,並且知足。
小分戒
45. 大王,比丘如何具足戒行呢?在此,大王,捨棄殺生之後,比丘戒除殺害生命。他放下棍棒和武器,心存良知地安住,充滿慈愛,關心一切眾生的幸福。這是他的戒行。
捨棄偷盜之後,他戒除拿取別人未給予之物。他只接受與期待他人給予之物,以清淨心過著誠實的生活。這也是他的戒行。
捨棄不淨行之後,他過著獨身的梵行生活。他遠離塵囂而住,戒除俗人的淫行。這也是他的戒行。
捨棄妄語之後,他戒除說謊。他只說實話,致力於真實地生活;他誠實、可信、不會欺騙世間的任何人。這也是他的戒行。
捨棄誹謗之後,他戒除挑撥離間。他不會將在此處聽到的話傳到別處,以便使別處的人與此處的人分裂;也不會將在別處聽到的話傳到此處,以便使此處的人與彼處的人分裂。他是被分裂的人們的調和者,是友誼的促進者。他欣喜、好樂、愉悅於和諧,只說促進和諧的話。這也是他的戒行。
捨棄粗話之後,他戒除粗言惡語。他只說輕柔、悅耳、親切、適意、文雅、和藹、眾人悅可的話。這也是他的戒行。
捨棄廢話之後,他戒除綺語。他在適當的時機才說話,說真實與有利益的話,說關於法與律的話。他的話可貴、適時、合理、慎重、與善法相關。這也是他的戒行。
他戒除傷害種子與植物的生命。
他只在一天裡的一段時間內取用食物,戒除在夜間及不適當的時間取用食物。
他戒除跳舞、唱歌、演奏音樂及觀看不適當的表演。
他戒除戴花環、以香水打扮及以油膏美化自身。
他戒除使用高及奢侈的床和椅。
他戒除接受金銀。
他戒除接受未煮之穀物、生肉、婦女與少女、男奴與女奴、山羊與綿羊、雞與豬、象、牛、馬與驢。
他戒除接受田地與土地。
他戒除為人傳遞訊息與辦理差事。
他戒除從事買賣。
他戒除涉及不實之秤重、假金屬及不實之度量器具。
他戒除賄賂、欺詐與詭計等不正當方法。
他戒除斷人手足、處人死刑、監禁他人、搶劫、掠奪與暴力。
這也是他的戒行。
中分戒
46.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一再地傷害種子與植物的生命──由根生、莖生、節生、芽生及種生的植物──他戒除傷害種子與植物的生命。這也是他的戒行。
47.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享用積存的物品,如:積存的食品、飲料、衣服、車乘、寢具、香水、可食之物──他戒除享用積存的物品。這也是他的戒行。
48.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觀看不適宜的表演,如:
呈獻舞蹈、歌唱、音樂演奏的表演;
戲劇表演;
民謠吟誦;
以鼓掌、鐃鈸、鼓演奏的音樂;
藝術展覽;
特技表演;
象、馬、水牛、公牛、山羊、公羊、公雞、鵪鶉的摶鬥;
棍戰、拳擊、摔角;
演習、點名、列陣、閱兵──
他戒除觀看這些不適宜的表演。這也是他的戒行。
49.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沉迷於下列這些遊戲與娛樂:
八列板戲;
十列板戲;
想像板戲;
踢石跳格子;
挑片遊戲;
骰子遊戲;
棍戲;
手指繪畫;
球戲;
吹管遊戲;
耍玩具犁;
翻觔斗;
耍玩具風車;
耍玩具度量器具;
耍玩具馬車;
耍玩具弓;
猜字遊戲;
猜意念遊戲;
模仿殘障者──
他戒除這些遊戲與娛樂。這也是他的戒行。
50.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享用高且奢侈的床和椅,如:
廣大睡床;
底座刻有動物形象的寶座;
長毛床單;
多色碎布拼揍的床單;
白色羊毛製的床單;
以花鑲邊的羊毛床單;
以棉花充填的被子;
有動物圖樣刺繡的羊毛床單;
單面或雙面有毛的羊毛床單;
鑲有珠寶的床罩;
絲綢床單;
舞廳地毯;
象、馬或馬車的小地毯;
羚羊皮小地毯;
芭蕉鹿皮製的精選床罩;
上有紅色布篷的床罩;
頭腳有紅色床墊的睡床──
他戒除使用這些高且奢侈的床和椅。這也是他的戒行。
51.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享用下列這些裝飾及美化他們身體的設備:在身上擦香粉;以油按摩;在香水中沐浴;按摩肢體;鏡子;油膏;花環;香水;軟膏;面粉;化妝品;手鐲;頭巾;有裝飾的拐杖;有裝飾的藥管;長劍;陽傘;鑲邊的拖鞋;頭巾式帽子;帶狀頭飾;犛牛尾製成的拂塵;長穗白袍──他戒除使用這些裝飾及美化身體的設備。這也是他的戒行。
52.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喜歡談論無關緊要的閒話,如:談論國王、盜賊與國家大臣;談論軍隊、災難與戰爭;談論食物、飲料、衣服與住所;談論花環與香水;談論親戚、車乘、村莊、鄉鎮、城市與國家;談論女人與談論英雄;街道言論與井邊言論;談論過去死亡的人;漫步扯談;關於世界與大海的推論;談論收入與損失──他戒除這些無關緊要的閒話。這也是他的戒行。
53.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從事爭吵辯論,(互相說道):
『你不了解法與律;我才了解法與律。』
『你怎麼可能了解法與律?』
『你的作法錯誤;我的作法才正確。』
『我是貫徹始終的;你是不貫徹始終的。』
『應該先說的你卻放在後面才說;應該放在後面說的你卻先說了。』
『你花費這麼長時間才想出來的理論已經被我駁倒了。』
『你的理論已經被駁倒了,你敗了。去!想辦法解救你的理論,或者若你辦得到的話,現在就使你自己脫離困境。』──
他戒除這些爭吵辯論。這也是他的戒行。
54.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為國王、大臣、王族、婆羅門、平民或青年傳遞訊息與辦理差事。(他們命令他):『來這裡;去那裡;拿這個去;帶那個來』──他戒除如此傳遞訊息與辦理差事。這也是他的戒行。
55.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從事詭計、漫談、暗示、貶低別人、以施望施。他戒除這些詭計與言談。這也是他的戒行。
大分戒
56.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藉著邪命、藉著低劣的技藝來維持生活,如:
看人四肢、手、腳等的痕跡來預言長壽、發達等,或相反的命運;
藉著預兆與徵象來占卜;
依閃電與天兆來占卜;
解釋夢境;
依身上的痕跡來算命;
依布被老鼠咬的痕跡來占卜;
做火供;
從杓中做供養;
供養莢、米粉、米粒、酥油與油給天神;
從口中做供養;
供養血牲給天神;
依手指尖來預言;
決定擬建房屋或園林的地點是否吉祥;
為國家大臣預言;
驅趕墳場的妖怪;
驅鬼;
住土屋者所宣說的咒術;
蛇咒;
毒術、蠍術、鼠術、鳥術、烏鴉術;
預言他人的壽命;
唸咒以保護他人不被箭所傷;
唸咒以了解動物的語言──
他戒除這些以低劣技藝而行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行。
57.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藉著邪命、藉著低劣的技藝來維持生活,如:解釋下列物品的顏色、形狀與其他特徵之含義,以決定它們預示其主人將會幸運或不幸:寶石、衣服、棍杖、劍、矛、箭、弓、其他武器、女人、男人、男孩、女孩、男奴、女奴、象、馬、水牛、公牛、母牛、山羊、公羊、雞、鵪鶉、鬣蜥蜴、耳環(或房屋的山形牆)、土龜或其他動物──他戒除這些以低劣技藝而行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行。
58.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藉著邪命、藉著低劣的技藝來維持生活,如作以下含意的預言:
國王將會前行;
國王將會返回;
我方國王將會進攻,敵方國王將會撤退;
敵方國王將會進攻,我方國王將會撤退;
我方國王將會戰勝,敵方國王將被擊敗;
敵方國王將會戰勝,我方國王將被擊敗;
如此,一方將會戰勝,另一方將被擊敗──
他戒除這些以低劣技藝而行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行。
59.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藉著邪命、藉著低劣的技藝來維持生活,如預言:將會有月蝕;日蝕;星蝕;日月將循著正常的軌道運行;日月將偏離軌道;星座將循著正常的軌道運行;星座將偏離軌道;將有流星墜落;將有天火;將有地震;將有地鳴;將有日、月與星的升起與落下、變暗與變亮;月蝕將造成如此的結果;日蝕將造成如此的結果;(等等,直到)日、月與星的升起與落下、變暗與變亮將造成如此的結果──他戒除這些以低劣技藝而行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行。
60.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藉著邪命、藉著低劣的技藝來維持生活,如預言:將有豐沛的雨量;將會乾旱;將會豐收;將會饑荒;將會安全;將有危難;將有疾病;將會健康;或者他們藉著會計、計算、估計、作詩與推論世界來活命──他戒除這些以低劣技藝而行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行。
61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藉著邪命、藉著低劣的技藝來維持生活,如:安排結婚的吉日;新娘何時迎回家及何時嫁出去;安排訂婚與離婚的吉日;安排儲錢與付錢的吉日;唸咒使人幸運或不幸;超渡墮胎的胎兒;唸咒以綁住某人的舌頭、麻痹他的下巴、使他的手失去控制、或使他變聾;藉著鏡子、女孩或天神來得到神諭似的答案;崇拜太陽;崇拜大梵天;從口中吐火;向幸運女神祈願──他戒除這些以低劣技藝而行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行。
62. 鑒於有些沙門及婆羅門依靠信眾供養的食物過活,卻藉著邪命、藉著低劣的技藝來維持生活,如:許下諾言要供養天神禮品,以報答他們的恩惠;實現這樣的諾言;信仰魔鬼;進入土屋後唸誦咒語;使人性能力增強或性無能;為房屋的地點作準備及灑淨;給予儀式的淨口與儀式的沐浴;供養犧牲之火;給予催吐劑、瀉劑、袪痰劑與化痰劑;給予耳藥、眼藥、鼻藥、洗眼劑及對抗藥膏;治療白內障、進行手術、做小兒科醫師;給予治療身體疾病的藥及對抗其副作用的藥膏──他戒除這些以低劣技藝而行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行。
63. 大王,如此具足戒行的比丘見到自己在持戒的各方面都沒有危險,就像一位已擊敗敵人的灌頂神聖戰士,見到沒有任何來自敵人方面的危險;同樣地,如此具足戒行的比丘見到自己在持戒的各方面都沒有危險。具備了如此聖潔的戒蘊,他內心體驗到無罪的快樂。大王,比丘如此具足戒行。
守護諸根
64. 再者,大王,比丘如何守護他的感官之門呢?在此,大王,眼見到物體之後,比丘不執取其形象或細部特徵。因為,如果他處於不收攝眼根的狀態,貪欲、憂傷等邪惡不善法將會侵襲他,所以他收攝、守護眼根,成就眼根律儀。耳聽到聲音之後……鼻聞到氣味之後……舌嚐到滋味之後……身觸到可觸知之物後……意認知精神對象之後,比丘不執取其形象或細部特徵。因為,如果他處於不收攝意根的狀態,貪欲、憂傷等邪惡不善法將會侵襲他,所以他收攝、守護意根,成就意根律儀。具足如此聖潔的諸根律儀之後,他內心感受到無缺點的快樂。大王,比丘如此守護諸根。
65. 大王,比丘如何具足正念與正知呢?在此,大王,向前行與返回時,比丘都以正知而行;向前看與向旁看時,他都以正知而行;彎曲與伸直肢體時,他都以正知而行;穿著袈裟、大衣與使用缽時,他都以正知而行;吃、喝、咀嚼、嚐味時,他都以正知而行;大小便時他都以正知而行;行走、站立、坐著、躺臥、覺醒、說話、沉默時,他都以正知而行。大王,比丘如此具足正念與正知。
66. 大王,比丘如何知足呢?在此,大王,比丘滿足於保護身體的袈裟與果腹的缽食,無論去到那裡,他都隨身只攜帶著(衣缽)。就像鳥兒一樣,無論飛到那裡,都只以兩翼為牠的唯一負擔;同樣地,比丘滿足於覆身的袈裟與果腹的缽食,無論去到那裡,他都隨身只攜帶著(衣缽)。大王,比丘如此知足。
67. 具足了此聖潔的戒蘊、聖潔的諸根律儀、聖潔的正念與正知及聖潔的知足之後,他前往寂靜的住處──森林、樹下、山丘、幽谷、山洞、墳場、叢林、空地、草堆。托缽回來,用過餐後,他盤腿而坐,保持身體正直,建立正念在自己面前。
68. 捨棄對世間的貪欲之後,他以無貪的心來安住,使心從貪欲中淨化出來。捨棄惡意與瞋恨之後,他以慈愛、關懷一切眾生幸福的心來安住,使心從惡意與瞋恨中淨化出來。捨棄昏沉與睡眠之後,他覺知光明、保持正念與正知地安住,使心從昏沉與睡眠中淨化出來。捨棄掉舉與追悔之後,他以舒坦、平和的心來安住,使心從掉舉與追悔中淨化出來。捨棄懷疑之後,他像已超越懷疑、對善法毫無疑惑之人那般地安住,使心從懷疑中淨化出來。
69. 大王,假使有一個人向別人借款來運用於自己的事業,並且事業成功,因此不但能清還舊債,而且剩餘的錢足以養活妻子。他會思惟此事,因而感到歡喜,心情愉快。
70. 再者,大王,假使有一個人生病、苦惱、重患,因而不能享用食物,體力衰退。過了一段時間,他從該病痊癒,能夠享用食物,並且恢復體力。他會思惟此事,因而感到歡喜,心情愉快。
71. 再者,大王,假使有一個人被囚禁在監獄。過了一段時間,他被釋放出獄,平安無險,並且財產沒有損失。他會思惟此事,因而感到歡喜,心情愉快。
72. 再者,大王,假使有一個人身為奴隸,沒有自主權,隸屬於別人,不能隨意到想去之處。過了一段時間,他被解除奴隸的身分,能夠自主,不再隸屬於別人,而是一個自由的人,能夠隨意到想去之處。他會思惟此事,因而感到歡喜,心情愉快。
73. 再者,大王,假使有一個攜帶財物的人,走在一條食物稀少、遍滿危險的荒野道路上。過了一段時間,他越過荒野,平安地到達一個安全無險的村莊。他會思惟此事,因而感到歡喜,心情愉快。
74. 同樣地,大王,當比丘見到自己內心的五蓋還未棄除時,他將之視為負債、患病、被監禁、身為奴隸、荒野的道路。
75. 然而,當他見到內心的五蓋已被棄除,他視之為還清債務、健康無病、獲釋出獄、免為奴隸、安全之地。
76. 當他見到內心的五蓋已被棄除時,內心就會生起愉快。當他內心愉快時,喜悅就會生起。當他內心充滿喜悅時,身體就會變得輕安。身體輕安之後,他就會感到快樂。由於快樂,他的心就會變得專注。
77. 他遠離感官欲樂,遠離不善法,進入並安住於有尋有伺、充滿由遠離而生起之喜樂的初禪。他以由遠離而生的喜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他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份不被此喜樂所充滿。
78. 大王,假設有一個善巧的侍浴者或他的學徒,將肥皂粉倒入金屬盆中,灑上水而將它揉捏成粉球,使得此肥皂粉球內外都被水分所滲透、包含、充滿,但還不至於有水滴下來的程度。同樣地,大王,他以由遠離而生的喜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比丘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份不被此喜樂所充滿。大王,這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79. 再者,大王,止息尋與伺之後,比丘進入並安住於伴隨著自信與定心、無尋無伺、充滿由定而生起之喜樂的第二禪。由定而生的喜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他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份不被此喜樂所充滿。
80. 大王,假設有一個湖水由底部湧上來的深湖。既沒有從東、西、南、北各方向而來的水流入此湖,也沒有時而降下的雨水注滿此湖,但是從湖底湧上來的一道冷水灌注、滲透、浸泡、充滿了這整個湖,因此這整個湖沒有任何部份不被冷水所充滿。同樣地,大王,由定而生的喜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比丘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份不被此喜樂所充滿。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81. 再者,大王,喜消退之後,比丘安住於平靜、正念與正知,並且他的身體感受到快樂。於是他進入並安住於聖者們所宣示:『他以平靜與正念快樂地安住。』的第三禪。此無喜之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他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份不被此樂所充滿。
82. 大王,假設在一個蓮花池中,有生於水中、長於水中、從未長出水外、就在水中繁茂的青色、白色、或紅色蓮花,冷水灌注、滲透、浸泡、充滿它們,從頂部到根部,因此那些蓮花沒有任何部份不被冷水所充滿。同樣地,大王,無喜之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比丘的全身,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份不被此樂所充滿。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83. 再者,大王,由於捨棄了樂與苦,以及先前喜與憂的消逝,比丘進入並安住於無苦無樂、具有因捨心而完全淨化之正念的第四禪。他以清淨、光明的心遍佈全身地坐著,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份不被清淨、光明的心所遍佈。
84. 大王,假設有人以白布從頭到腳覆蓋自己地坐著,使得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份不被白布所遍佈。同樣地,大王,比丘以清淨、光明的心遍佈全身地坐著,因此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份不被清淨、光明的心所遍佈。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85.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智見。他了解到:『這是我的身體,擁有色身,由四大所組成,源自父親與母親,依靠飯與粥來增進它、它是無常的、會受到觸痛與壓迫的、會解體與分散的。而這是我的心,依靠色身的支持,並且與色身有密切關係。』
86. 大王,假設有一顆具有最純淨光澤的美麗綠寶石、它具有八個截面、精雕細琢、透明、清澈、完美無瑕、具足一切優越的品質,而且有一條青、黃、紅、白或棕色的線穿過其中,視力敏銳的人將它拿在手中,會如此思惟它:『這是一顆具有最純淨光澤的美麗綠寶石、它有八個截面、精雕細琢、透明、清澈、完美無瑕、具足一切優越的品質,而且有一條青、黃、紅、白或棕色的線穿過其中。』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智見。他了解到:『這是我的色身,由四大所組成,源自父親與母親,依靠飯與粥來增進它、它是無常的、會受到觸痛與壓迫的、會解體與分散的。而這是我的心,依靠色身的支持,並且與色身有密切關係。』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87.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造成意生身。由本來這個身體,他能變出另一個具足色法、由心意所生、一切器官俱全、諸根完整無缺的身體。
88. 大王,假設有人將蘆葦從它的莢中抽出來,他會想著:『這是蘆葦,這是莢。蘆葦是蘆葦,莢是莢,它們是不同的東西;但是蘆葦是從莢中抽出來的。』或者假設有人將劍從劍鞘中抽出來,他會想著:『這是劍,這是劍鞘。劍是劍,劍鞘是劍鞘,它們是不同的東西;但是劍是從劍鞘中抽出來的。』或者有人將蛇從牠的蛻皮中拉出來,他會想著:『這是蛇,這是蛻皮。蛇是蛇,蛻皮是蛻皮,它們是不同的東西;但是蛇是從蛻皮中拉出來的。』同樣的,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造成意生身。由本來這個身體,他能變出另一個具足色法、由心意所生、一切器官俱全、諸根完整無缺的身體。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89.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神變智。他能夠顯現各種神變智:他能從一身變成多身,從多身變成一身;自在地出現與隱沒;毫無障礙地穿過城牆、壁壘、山丘,猶如穿過空間一般;鑽入與鑽出土地,猶如出入於水一般;在水面上行走而不會沉沒,猶如在地上行走一般;盤腿坐著遨遊於空中,猶如飛鳥一般;以手觸摸日月,如此神通廣大;他能使身體通行無阻地去到梵天界。
90. 大王,假設有一位善巧的陶藝家或他的學徒,要將已調製好的黏土塑造他想塑造的器皿;或者善巧的象牙雕刻師或他的學徒,要將已處理好的象牙雕刻成他想雕刻的作品;或者善巧的金匠或他的學徒,要將已處理好的金子製作成他想製作的作品;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神變智,他能夠顯現各種神變智。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91.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天耳智。以清淨、超越人耳的天耳,他能夠聽見兩種聲音:天界的聲音與人界的聲音,遠處的聲音與近處的聲音。
92. 大王,假設有人在大路上旅行,他聽見定音鼓、小鼓、喇叭、鐃鈸與大鼓的聲音,心裡會想:『這是定音鼓的聲音,這是小鼓的聲音,這是喇叭、鐃鈸與大鼓的聲音。』同樣地,大王,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天耳智。以清淨、超越人耳的天耳,他能夠聽見兩種聲音:天界的聲音與人界的聲音,遠處的聲音與近處的聲音。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93.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他心智。當他以自己的心來涵蓋別人的心時,他能夠了解其他眾生與其他人的心。對於有貪欲的心,他了解它為有貪欲的心;對於無貪欲的心,他了解它為無貪欲的心。對於有瞋恨的心,他了解它為有瞋恨的心;對於無瞋恨的心,他了解它為無瞋恨的心。對於有愚痴的心,他了解它為有愚痴的心;對於無愚痴的心,他了解它為無愚痴的心。對於狹隘的心,他了解它為狹隘的心;對於散亂的心,他了解它為散亂的心。對於高尚的心,他了解它為高尚的心;對於不高尚的心,他了解它為不高尚的心。對於可超越的心,他了解它為可超越的心;對於不可超越的心,他了解它為不可超越的心。對於專注的心,他了解它為專注的心;對於不專注的心,他了解它為不專注的心。對於解脫的心,他了解它為解脫的心;對於未解脫的心,他了解它為未解脫的心。
94. 大王,假設有喜愛裝飾的少男或少女,對著一面清淨明亮的鏡子或一碗清澈的水,細看自己臉部的映像。如果臉上有痣,自己會知道:『臉上有痣。』如果臉上沒有痣,自己會知道:『臉上沒有痣。』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他心智。當他以自己的心來涵蓋別人的心時,他能夠了解其他眾生與其他人的心。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95.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宿命智。他能夠回憶自己的許多過去生,即:一生;兩生;三、四或五生;十、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生;一百生、一千生、十萬生;許多成劫、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與壞劫。(他憶念):『那時,我有如此的名字,屬於如此的家族,有如此的長相;吃如此的食物,經歷如此的苦樂,有如此長的壽命。那一生死亡之後,我又投生於某處,在那一生,我有如此的名字,屬於如此的家族,有如此的長相;吃如此的食物,經歷如此的苦樂,有如此長的壽命。那一生死亡之後,我又投生於此處。』他能如此憶念許多過去生的生活型態與細節。
96. 大王,假設有人從自己的村莊去到別的村莊,再從那個村莊去到另一個村莊,然後從該村莊回到自己的村莊,他心裡會想:『我從自己的村莊去到那個村莊,那時我如此站著,如此坐著,如此說話,如此沉默。我從那個村莊又去到另一個村莊,在那裡,我如此站著,如此坐著,如此說話,如此沉默。從該村莊,我回到自己的村莊。』同樣地,大王,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宿命智。他能憶念許多過去生的生活型態與細節。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97.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觀眾生死生的智慧。以清淨的、超越人眼的天眼,他見到眾生死亡與再度投生──低賤與高貴、美麗與醜陋、幸運與不幸──他了解眾生如何依照自己的業而承受果報,他見到:『這些眾生具有身、口、意的惡業──他們誹毀聖者,秉持邪見,依邪見而造作──他們身壞命終、死亡之後投生於惡道、苦趣、下界、地獄。而另外這些眾生具有身、口、意的善業──他們不誹毀聖者,秉持正見,依正見而造作──他們身壞命終、死亡之後投生於善趣、天界。』如此以清淨的、超越人眼的天眼,他見到眾生死亡與再度投生──低賤與高貴、美麗與醜陋、幸運與不幸──他了解眾生如何依照自己的業而承受果報。
98. 大王,假設在一個中央廣場有一棟具有樓上陽台的建築物,視力敏銳的人站在陽台上可以看到人們進入屋子、離開屋子、在街上行走、坐在中央廣場上。他心裡會想:『那些人正走進屋子,那些人正走出屋子,那些人正在街上行走,那些人正坐在中央廣場上。』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觀眾生死生的智慧。他以清淨的、超越人眼的天眼見到眾生死亡與再度投生,他了解眾生如何依照自己的業而承受果報。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
99.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漏盡智。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的原因。』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的息滅。』他如實地了知:『這是導致苦息滅之道。』他如實地了知:『這些是諸漏。』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諸漏的原因。』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諸漏的息滅。』他如實地了知:『這是導致諸漏息滅之道。』
如此知見,他的心從欲漏、有漏、無明漏當中解脫出來。心解脫之後,如此的智慧就會生起:『心已經解脫。』他了知:『生已滅盡,梵行已立,應作皆辦,不受後有。』
100. 大王,假設在山谷中有一座湖,湖水清澈、澄淨、無垢。視力敏銳的人站在湖邊可以看見蠔貝、沙、卵石、游動與靜止的魚群。他心裡會想:『這座湖的水清澈、澄淨、無垢,水中有蠔貝、沙、卵石、游動與靜止的魚群。』
同樣地,大王,當比丘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漏盡智。他如實地了解:『這是苦。』……他了知:『生已滅盡,梵行已立,應作皆辦,不受後有。』大王,這也是比前面那些更殊勝與崇高的可見之沙門果。大王,再也沒有比這種更殊勝與崇高的其他沙門果了。」
阿闍世王自誓為在家弟子 回首頁
101. 世尊說完之後,阿闍世王告訴世尊說:「太美妙了,尊者!太美妙了,尊者!就像將翻覆之物翻轉復正,使隱匿之物揭示顯露,為迷路之人指示正途,為黑暗中之人擎舉明燈,使他們得以見物;同樣地,尊者,世尊以種種方式宣說佛法。從今日起我歸依世尊、歸依法、歸依比丘僧團,願世尊接受我為從今天開始終身歸依之在家信徒。
尊者,罪惡戰勝了我,我是如此愚痴、如此迷惑、如此笨拙,為了王位,我殺害了自己的父親,那樣一位正直的人、正直的君王。請世尊確認我的罪過為罪過,以便未來我能夠以戒律約束自己。」
102. 「如是,大王,罪惡戰勝了你,你是如此愚痴、如此迷惑、如此笨拙,為了王位,你殺害了自己的父親,那樣一位正直的人、正直的君王。然而,既然你已經見到自己的罪過為罪過,並且願意依法改正,因此我確認此事。大王,這就是在聖者的戒律中成長:一個人能見到自己的罪過為罪過,依法改正,以及在未來成就自制。」
103. 世尊如此說過之後,阿闍世王告訴世尊說:「尊者,現在我必須回去了,我還有許多任務與職責在身。」
「隨適宜而行,大王。」
阿闍世王對世尊的開示感到歡喜,並向世尊致謝。從座位上起身,禮敬世尊,右繞三匝,然後離去。
104. 阿闍世王離開之後,世尊對眾比丘說:「諸比丘,這位國王毀了自己、傷了自己。諸比丘,如果這位國王不殺害自己的父親,那樣一位正直的人、正直的君王,那麼,就在這一個座位上,他能夠生起無塵無垢的法眼。」
世尊如此說完之後,諸比丘內心愉快,對世尊的話感到歡喜。
(沙門果經至此結束)
回首頁
Ⅱ. 註疏篇
回首頁
沙門果經註疏
(The
Commentarial Exegesis of the Sāmaññaphala Sutta)
(註:註釋書。疏:疏鈔,乃是進一步解說註釋書內容的書。新疏:新疏鈔,乃是解說註或疏之內容的書。註疏篇所用的節數號碼與經文篇所用的相同,要了解某段經文的解釋時,可依循相同節數號碼在註疏篇中查到,經文的文句將以較粗的楷書體字顯示。註疏中方括弧裡的詞語乃是補充自疏鈔或新疏鈔;疏鈔中方括弧裡的詞語乃是補充自新疏鈔;圓括弧裡的詞語乃是英文譯者所添加。)
1. 在耆婆王子育的芒果園
註:當經上提到:「世尊住在王舍城,耆婆王子育的芒果園。」時應當如此理解:世尊住在耆婆王子育的芒果園,而該芒果園位於王舍城的附近。「耆婆王子育」的意思是:被王子撫養的一個活著的人。當耆婆還是個嬰兒時,他被母親遺棄。眾人見到許多烏鴉環繞著一個嬰兒,並且發現嬰兒還活著,因此為他取名為耆婆(Jīvaka;意為「活著」)。他被送入皇宮,由皇家的褓姆養育他。如此,因為他被王子撫養,所以稱他為王子育(Komārabhacca)。耆婆的故事詳細地記載於律藏的犍度品中,律藏的註釋《普端嚴註》(Samantapāsādikā)並加以解釋。
有一次,世尊得了一種血液疾病,耆婆用瀉劑治好世尊的病。那時他供養佛陀一套高價的袈裟,當佛陀講說致謝的開示時,耆婆證悟了初果須陀洹。因此他心裡想:「我每天應當來侍奉佛陀兩、三次,但是竹林精舍離這裡太遠,我的芒果園比較近,且讓我在芒果園中建造世尊的住處。」他建造了夜間住處、日間住處、山洞、小屋、亭榭等等,建造了一座適合世尊居住的香舍,並且在芒果園的周圍建起一道十八碼高的圍牆。他邀請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接受他飲食及袈裟的供養。在傾注供水之後,他獻出了此住處。
摩羯陀國的阿闍世王 回首頁
註:(在他出生之前被諮商的)占星家預言:「即使在他還未出生(ajāta)之時,他就已經是國王的怨敵(sattu)了。」因此(他被取名為)阿闍世──「未生敵」。
據說當他還在母親的子宮內時,王后(他的母親)心中生起一個強烈的欲望,想要喝國王右手臂的血。她心裡想:「這個欲望太可怕了!我不可以跟任何人講。」由於不能表達出此欲望,她變得憔悴與蒼白。國王問她:「愛卿,是什麼原因使妳的身體變得憔悴蒼白?」──「請不要問我,大王。」──「愛卿,如果妳不能將妳的心事傾訴給我聽,那麼還有誰能聽妳傾訴呢?」國王以種種方法催促她,說服她說出來。聽完她的話之後,國王說:「愛卿,為什麼妳會認為這是可怕的事情呢?」於是他召來御醫,叫御醫用金色的刀在他右手臂上劃開一道傷口,以金色的碗裝盛血液,再以水混合之後,送給王后喝。
占星家聽到這件事之後,宣布說:「王后子宮內的胎兒是國王的怨敵,他將會殺害國王。」王后聽到這消息,心裡想:「他們說我腹中的這個嬰兒出生之後,將來會殺害國王。」因為想要墮胎,她就到公園去,叫人踐踏她的腹部;但是並沒有成功。她一再地到公園去,用同樣的方法做。國王問她說:「妳為什麼經常到公園去?」知道原因之後,國王說:「愛卿,我們甚至還不知道妳子宮內所懷的是男孩或是女孩,如果我們如此對待我們的孩子,大災難將會降臨我們的國土。不要再如此做!」如此勸阻她之後,他派一名警衛看守她。當嬰兒出生時,她心裡想:「我要殺死他。」但是警衛將嬰兒抱走了。過了一段時間,當王子成長之後,他們帶他來見王后。當她見到王子,母愛在她的心中生起,她再也不忍心殺害他了。後來,國王冊封王子為副國王。
有一次,提婆達多在獨處時心裡想:「舍利弗有一團隨從,目犍連有一團隨從,摩訶迦葉也有一團隨從,他們每個人都保有自己的隨從;我也應該召集隨從。」他又想:「沒有人供養的話不可能獲得隨從。我應當謀取供養。」於是,正如在《犍度品》中所記載的,藉著神通變化,他取得阿闍世太子的信任。阿闍世太子早晚都帶著五百輛馬車來伺候他。知道太子已經完全信任他之後,有一天,提婆達多去見太子,對太子說:「太子,古代的人長壽,現代的人短壽;因此你應當殺掉你的父親,自己成為國王;我則會殺掉世尊,自己成為佛陀。」他如此吩咐太子殺害自己的父親。
太子心裡想:「提婆達多大師神通廣大、無所不知。」於是他將一把短劍綁在腿上,中午時進入國王的內宮。但是由於害怕、憂慮、驚恐、擔心,他把〔提婆達多〕所教的指示弄混淆了。大臣們逮捕他,並且審問他。他們爭論是否應將太子連同提婆達多與〔提婆達多同黨的〕所有比丘處死。最後決定聽從國王的指示,因此他們將此事報告國王。
國王將主張處死太子與提婆達多的那些大臣降級,而將反對處死他們的那些大臣升級。他問太子:「太子,你為什麼要殺我?」──「我想要你的國家,陛下。」國王就將國家交給他。
太子報告提婆達多說國王已經讓他達成所願了。提婆達多說:「就像有人只是將胡狼關進籠子就擊鼓示慶一樣,你以為自己已經完成任務了。再過不了幾天,當國王想起你對他的蔑視時,他就會將王位奪回。」──「那麼,我應當怎麼辦呢?尊者。」──「斬草除根,殺掉他!」──「但是,尊者,我不應當以武器殺死我的父親,不是嗎?」──「那麼就斷絕他的食物,讓他餓死。」
太子將他的父親關進酷刑的監牢,那是一間用來施加刑罰的燻製房。他下令:「除了我的母親之外,不要讓任何人來見他。」王后將米飯盛在金色的器皿中,將該器皿安置在自己的臀部上方,如此進入監牢。國王吃了米飯,因此得以繼續存活。太子問國王:「父親,為什麼你能繼續存活?」知道了原因之後,他下令:「不要讓我的母親臀部上帶任何東西進來。」從那時起,王后將器皿放在她的頂髻中進入監牢。知道此事之後,太子下令:「不要讓她頭髮綁著頂髻進去。」於是她將米飯裝在一雙金色的鞋子裡,封好鞋子,穿著它們進入監牢。如此,國王得以繼續存活。太子又問國王,為什麼他還能活著。知道原因之後,他下令:「不要讓她穿著鞋子進去。」從那時起,王后以香水沐浴之後,將四種糖〔凝乳、蜂蜜、酥油、糖漿〕塗抹於身上,穿好衣服,然後進入監牢。國王藉著舔她身上的糖蜜而繼續存活。太子又再度詢問,知道原因之後,他下令:「從今以後,禁止我的母親進入監牢。」王后站在監牢門外大聲叫喚道:「哦!我的丈夫頻婆娑羅,在他還是嬰兒的時候,你不讓我殺他,你養育了你自己的怨敵。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從今以後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如果我曾經做錯任何事情,請原諒我吧,大王!」她痛哭流淚地走了。
從那時開始,國王就得不到任何食物了。但是他藉著來回地經行,處在(須陀洹)道果的快樂中,而能繼續存活。他的身體煥發著光芒。
太子問他:「父親,你為什麼還能活著?」知道了他藉著來回地行走而繼續存活,並且見到他的身體變得光芒煥發之後,太子心裡想:「現在,我要讓他不能來回地行走。」他命令理髮師說:「用剃刀把我父親的腳切開,塗上鹽和油,然後放在燒得火紅無煙的刺槐木火炭上烤。」
當頻婆娑羅王看見理髮師來到時,他心裡想:「想必是有人通知了我的兒子,所以他們要來幫我修剪鬍子。」他們走向頻婆娑羅王,向他頂禮,然後站起來。他問說:「為什麼你們來到這裡?」他們稟告他們所接收到的命令。頻婆娑羅王說:「你們應當照著你們國王的命令去做。」他們請他坐下來,再次向他頂禮,然後說:「陛下,我們只是按照國王的命令行事,請不要見怪。如此對待像您這樣一位正直的國王是不對的。」於是他們用左手抓住他的足踝,用右手握住剃刀,切開他的腳,塗上鹽和油,然後放在燒得火紅無煙的刺槐木火炭上烤。(由於這種酷刑)頻婆娑羅王感到劇烈的痛苦。在憶念佛、法、僧的當下,他像拋在佛塔平台上的花環那般地枯萎了。死後他投生於四大王天,成為毘沙門天王隨眾中的一名天神,名叫闍尼沙(Janavasabha)。
就在那天,阿闍世王的一個兒子誕生了。兩封信同時送到他那裡:一封是關於他兒子的誕生,另一封是關於他父親的死亡。大臣們心裡想:「我們應該先稟告他關於他的兒子誕生之事。」於是先將那封信遞呈給他。就在(他讀信的)那一刻,他的心中生起對新生兒子的父愛,那種愛使他全身震動,並且穿透到他的骨髓。在那一刻,他體會到作父親的滋味。他以了解:「當我出生時,我的父親也同樣對我生起如此的愛。」他下令:「來人!去將我的父親釋放了吧。」他的部下稟告說:「我們怎麼可能釋放他呢?陛下。」並且將另一封信呈交給他。
一知道父親死亡的消息之後,他立刻去見母親,問她說:「母親,在我出生之後我的父親愛我嗎?」他的母親說:「傻孩子,你在說什麼?當你還小的時候,有一次,你的手指上長了一顆小膿皰。你一直哭泣,他們撫慰你,但是沒有人能讓你平靜下來,所以他們帶你到判事廳去見你的父親。你的父親將你的手指放進他的口中,而那個膿皰就在你父親的口中破開了。他不能將膿血吐出來,基於對你的愛,他將膿血吞進去了。這就是你的父親對你的愛。」阿闍世王痛哭、悔恨地處理了他父親的屍體。
之後,提婆達多來見阿闍世王,要他派幾個人去暗殺佛陀。他派遣了幾個人給提婆達多(,但是計畫失敗了)。接著,提婆達多親自爬上靈鷲山,用吊索吊起一塊岩石,向佛陀猛擲而去(,但是該計畫也失敗了)。他甚至令人放出那拉奇林大象(去攻擊佛陀)。然而,無論他使用什麼方法,都無法殺害世尊。當他喪失名譽及供養之後,他請求佛陀接受他的五項提議,佛陀不答應,而提婆提多則利用這五項作標榜,贏得不少比丘的支持。他造成僧團分裂,但是舍利弗與目犍連去到他的住處,使跟隨他走的那群比丘再度對佛陀生起信心,並且將他們帶走。當提婆達多知道此事時,他當場口吐熱血。
躺臥在病榻九個月之後,提婆達多心中充滿悔意。他問道:「導師現今住在何處?」當他們告訴他佛陀住在竹林精舍時,他說:「那麼就連床將我抬去,我要見導師。」然而,由於他所造的惡業,使得他無法再見到世尊。當他抬到竹林精舍的蓮花池旁時,大地裂開,而他即墮入到大地獄之中。這是簡短的解說,詳細的說明記載於《犍度》中(小品.七)。
如此,此國王被取名為「阿闍世」,因為占星家預言說:「即使在他還未出生之時,就已經是國王的怨敵了。」
阿闍世王正坐在皇宮上層的陽台
註:為什麼他要坐在那裡呢?為了要避開睡眠。因為自從他殺害自己的父親之後,每到睡覺的時間,他一閉上眼睛就感覺猶如被一百支矛戳刺身體一般,會痛哭著醒起來。別人問他怎麼回事時,他回答說:「沒什麼。」從那時起,他就很厭惡睡眠。因此他坐在陽台上以避開睡眠。
阿闍世王發出如此的歡喜讚歎
註:正如桶中容納不下的油會流溢出來,而被稱為浮油;池湖中容納不下的水會氾濫到土地上,而被稱為洪水;同樣地,當心中容納不下歡喜的情緒時,那情緒變得太強烈,而無法維持在心中,於是發出為言語,這稱為「歡喜讚歎」(udāna)。
我們是否能拜訪那一位能沙門或婆羅門
註:阿闍世王以這句話來暗示。暗示誰呢?暗示耆婆。為了什麼目的呢?為了要見世尊。然而,難道他不能自己去見世尊嗎?不能。為什麼呢?因為他造了嚴重的惡業。因為他殺害了自己的父親,而他的父親正是世尊的聖弟子及擁護者;反之,他自已則擁護屢次要傷害世尊的提婆達多。如此,他造了嚴重的惡業,所以他不能自己去見世尊。而耆婆是世尊的擁護者,所以他暗示耆婆,他心裡想:「我要像他的影子一般(跟著耆婆)去見世尊。」
耆婆了解阿闍世王給他暗示嗎?是的,他了解。那麼,為什麼他保持沉默呢?為了避免被打斷。因為他心裡想:「在這個集會中,有許多人是外道六師的擁護者,由於他們所擁護的導師是沒有修養的,他們本身自然也是沒有修養的。一旦我開始談論世尊的功德,他們就會站起來,打斷我的話,而談論他們自己導師的功德。但是由於國王已曾親近他們所擁護的導師,國王對他們所談論(他們導師)的功德將不會感到滿意,因為他知道這些言論是沒有真實意義的。然後他就會問我,我就能不被打斷地解說世尊的功德,並帶領國王去見世尊。因此,雖然他了解(暗示),他仍然保持沉默,以避免被打斷。
大臣們心裡想:「今天國王以五種方式讚歎月夜,他一定是想要親近沙門或婆羅門,諮詢問題以及聽聞教法。他會對教法能激起他信心的(沙門或婆羅門)恭敬有加,而所擁護的沙門獲得皇家支持的大臣將會很幸運。」內心存在如此的動機之後,每個大臣都想著:「我要稱讚我所擁護的沙門,並且帶領國王去見他。」於是他們一個個地開始稱讚自己所擁護的沙門。
2-7. 外道六師
(1)布蘭迦葉:布蘭(Pūraṇa)是這個導師的名字,迦葉(Kassapa)是他的姓。他之所以被取名為布蘭(「圓滿」)的原因據說是:他出生在一個擁有九十九個奴隸的家族,他出生了正好圓滿幸運的數目(一百),所以他被取這個名字。因為他是幸運的奴隸,所以沒有人會指使他:「這做得好。」或「這做得不好。」或「這應該做。」或「這不應該做。」他心裡想:「我為什麼要留在這裡?」因此他逃走了。小偷竊取了他的衣服。由於不知道如何用樹葉或草葉來遮蓋身體,所以他裸體入村。人們看見他之後心裡想:「這位沙門是少欲的阿羅漢,沒有人像他這樣。」於是他們帶著糕餅、米飯等來供養他。從那時起,即使得到衣袍,他也不穿,因為他知道:「正因為我不穿衣服,所以才得到這件衣袍。」他將〔他的裸體〕當作出家(pabbajjā)。有不同群體的五百人跟隨他出家,因此說:「布蘭迦葉,他是教團之首」等等。
阿闍世王沉默不語
註:當一個人想要吃甜蜜、金色的芒果時,如果有人交給他一顆苦澀的木槌果,他一定不會感到滿意的。同樣地,阿闍世王想要聽聞有關禪那、各種神通等功德,以及具備三種特徵的甜蜜佛法開示,當然對有關布蘭迦葉功德的言論感到極端不滿意,因為他之前就曾經見過布蘭迦葉,那時就已經對他的教法感到不滿意了,所以他保持沉默。雖然感到不滿意,他還是默默地容忍自已不歡喜聽的言論,因為他知道:「如果我責備那個大臣,以及命令人抓住他的脖子,將他趕出去,那麼其他人都會害怕相同的命運會降臨在他們的身上,因而沒有人敢再說話了。」然而,由於他保持沉默,另一個大臣心裡想:「我要稱讚我自己擁護的沙門。」於是他開始講話。
(2)末伽梨瞿舍梨:末伽梨是他的(本)名,他的第二個名字瞿舍梨(Gosāla.牛舍的)源自他出生於瞿舍梨〔村〕;〔然而,有人說他出生於牛舍中。〕據說當他拿著一鍋油要走過泥濘地時,他的主人大聲地呼喊他:「不要絆倒!(mā khali.末伽梨)」由於不小心,他絆跤而跌倒了。因為懼怕他的主人,他開始逃跑。他的主人追趕他,並且抓住他的衣角。他就捨棄衣服,裸體逃走。其餘的情況與布蘭迦葉的故事相同。
(3)阿耆多翅舍欽婆羅:阿耆多是他的名字,而他穿著一件髮毯(kesakambala.翅舍欽婆羅)。所謂「髮毯」就是用人的頭髮編成的毯子。沒有其他衣物會比髮毯更令人厭惡了,因為佛陀說:「諸比丘,在一切編織的衣物當中,髮毯是最令人厭惡的。髮毯在冬天穿起來很冷,在夏天穿起來很熱,而且難看、惡臭、觸感不舒服。」(增支部.3:135/i.286)
(4)波拘陀迦旃延:波拘陀是他的名字,迦旃延是他的姓。他拒絕使用冷水,即使在他解完大便之後,他也不用冷水來洗淨,而用熱水或油來洗淨。如果在路上他經過河流或水坑,他會想著:「我的戒已經破了。」於是他藉著堆起一堆沙丘來恢復他的戒,然後繼續他的路程。他執持不幸論(nissirīkaladdhika)。
(5)薩若毘耶梨弗:他的名字叫薩若,他是毘耶梨的兒子(putta.弗或子),所以稱為薩若毘耶梨弗。
(6)尼乾陀若提子:他稱為尼乾陀(Nigaṇṭha.無結者),因為他聲稱他的教義是:「我們沒有煩惱結,沒有煩惱縛,我們沒有煩惱纏。」他是若提的兒子,所以稱為若提子。
耆婆之言
8. 聽完他們的陳述之後,阿闍世王心裡想:「我不想聽正在說話者的陳述;我想聽就像在龍國之中的金翅鳥一般正保持沉默者的陳述。這些言論對我沒有利益。」然後他心裡想:「耆婆是世尊的擁護者,世尊是安詳者,耆婆本人也很安詳,所以他像具足戒行的比丘一般,默然地坐著。除非我問他,否則他不會先開口,就像大象踐踏(陷阱)時,牠的腳必定會被抓住一般。」因此他採取主動地諮詢耆婆,問說:「賢友耆婆,你為什麼保持沉默?當這些大臣各自稱讚自己所擁護的沙門時,你一句話也沒說。難道你不是像他們一樣也擁護某一位沙門嗎?你很貧窮嗎?難道我的父親沒有發給你奉祿嗎?或者你對任何人都沒有信心?」
這時耆婆心裡想:「國王要我講述我所擁護之沙門的功德,這不是我保持沉默的時候了,但是我不應用這些大臣講述他們導師功德的方式來講述佛陀的功德──即:先禮拜國王,然後坐下來講。」因此,他從座位上站起來,朝著世尊所在的方向頂禮,恭敬地雙手合掌,舉起到與額頭相等的高度,然後說:「大王,不要認為我不加以選擇地親近任何沙門。因為當我的導師入胎時、出胎時、出家時、成道時、初轉法輪時,一萬個世界都震動;當他顯現雙神變,以及(在天界教完阿毗達摩而)從天界回到人間時,世界同樣地震動。我將講述導師的功德,請一心專注地聆聽,大王。」如此說過之後,他開始講述:「陛下,世尊是阿羅漢、圓滿覺悟者、明行足、」等等。
當耆婆解釋了每一種德號的意義之後,他說:「如此,大王,我的導師是阿羅漢、圓滿覺悟者、明行足……世尊,陛下應當拜訪世尊。陛下若拜訪他,或許他能帶給陛下內心安寧。」他如此說的意思是:「大王,即使有一百個、或一千個、乃至十萬個像您這樣的人提出問題,佛陀還是能夠了知他們的心,以及回答他們的問題。大王,您應當充滿信心地去親近佛陀,並提出您的問題。」
9. 當阿闍世王聽到有關世尊功德的言論時,他的全身立刻充滿了五種喜,就在那個當下,他很想去見世尊。他心裡想:「如果此刻我要去見佛陀的話,除了耆婆以外,沒有人能夠很迅速地將交通工具準備好。」因此他說:「那麼就將象乘準備妥當吧!耆婆。」
在各種交通工具之中,象乘是最好的。既然要去見最好的人,就應當坐最好的交通工具去。再者,馬乘及馬車等的聲音很吵,遠遠就能聽見它們的聲音;而象乘則是一步一步地前進,因此聽不到任何聲音。想到應當乘坐安詳、寧靜的交通工具去見安詳、寧靜的世尊,因此阿闍世王下令準備象乘。
耆婆不用任何人指示,單憑他自己的深謀遠慮來準備象乘,因為他心裡想:「國王說這時候要外出,然而國王有很多敵人;萬一路上發生了某些障礙,人們會指責我在不適當的時間帶領國王外出,而且他們會指責世尊沒有考慮適當時間就為國王說法。所以我應當為國王做好妥當的防衛,才不至於有人指責我或世尊。」
再者,在女人的擁護之下,男人就不會感到害怕。因此,為了讓國王在眾王妃的環繞之下快樂地向前行,耆婆準備了五百隻雌象。他交代國王的五百名王妃裝扮成男人的模樣,手中持著劍與矛,坐上這些象,擁護著國王。他進一步想到:「國王沒有在今生證得道果的助緣;而諸佛只在他們見到(聽眾)有助緣的情況下說法。所以我應當召集群眾去聽法,因為那樣的話,當佛陀見到有助緣的人,他就會說法,這將能令大眾受益。」因此他令人到處發出通告:「今天國王要去見世尊,每個人可盡自己的能力來保護國王。」
將國王的隨從安排妥當之後,耆婆本人走近國王,同時心裡想:「萬一有任何危險發生,我將是第一個犧牲性命來保護國王的人。」然而,已經有那麼多人執持火炬擁護──成千上百,難以計算。
10. 阿闍世王突然被恐怖、疑懼與驚駭所籠罩等等
註:在此,怖畏有四種,即:心怖畏(cittutrāsabhaya)、智怖畏(ñāṇabhaya)、所緣怖畏(ārammaṇabhaya)以及愧怖畏(ottappabhaya)。在這四種當中,下列這段經文所指的是心怖畏:「因為有生,所以怖畏、鬥爭等生起。」下列這段經文所說的是智怖畏:「那些(天神)聽聞如來所說的法之後,全部生起怖畏、悚懼心與恐懼。」(《相應部》22:78/iii.85)下列這段經文所說的是所緣怖畏:「這就是即將來臨的怖畏與恐懼嗎?」(《中部》4/i.21)下列這段經文所說的是愧怖畏:「在此情況下,他們稱讚怖畏,而不稱讚勇氣;因為由於怖畏,所以善人不造惡業。」(《相應部》4:33/i.21)在這四種怖畏當中,此處指的是心怖畏。
疏:心怖畏本身就是具有害怕意思的怖畏。智怖畏是當可怕的對象(或情況)顯現為可怕時,仔細觀察它為可怕的,了解到:「這是應當怖畏的。」在此,有人會問:「那麼,智怖畏(本身)這個智慧會不會感到害怕呢?」答案是:不會感到害怕。因為它只是單純地判斷:過去的諸行已經滅、現在的諸行正在滅、未來的諸行將會滅。(《清淨道論》第21章.第32節)所緣怖畏乃是造成怖畏生起的某種事物。愧怖畏乃是藉著它人們害怕造作惡業。
註:然而,為什麼阿闍世王會感到怖畏呢?因為芒果園寂靜無聲使他懷疑耆婆圖謀不軌,所以他感到怖畏。據說,在皇宮的上層陽台時,耆婆就已經告訴阿闍世王:「大王,世尊喜歡寧靜,我們應當靜靜地去見他。」因此阿闍世王禁止沿途演奏音樂;樂器只是帶著備用而已。而且他們也不大聲說話,只是以彈指作為信號而向前進行。在芒果園中,連打噴嚏的聲音都沒有;一般而言,作國王的都喜歡聽聲音,他對芒果園的寂靜感到不安,接著就對耆婆生起如此的疑心:「這個耆婆告訴我芒果園裡住著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但是現在這裡卻連打噴嚏的聲音都聽不到,他一定在說謊。因為他想要奪取王位,所以欺騙我,帶領我離開京城,而他在前面埋伏了軍隊,準備逮捕我。他本人有五隻象的力量,而且緊靠在我旁邊行走,而我身邊卻連一個武裝的衛兵也沒有。哦,我真的是要遭殃了!」由於他感到非常害怕,所以無法表現出無畏的樣子,而向耆婆說出了自己的怖畏。
耆婆心裡想:「國王不了解我,他不了解我耆婆是不會殺害生命的。如果我不設法使他安心,他將會暴斃死去。」因此他安撫國王,說道:「不要害怕,大王,」等等。他說:「向前走!」說了兩次,催促國王繼續向前,因為如果他只說一次,語氣就不夠堅定。他指出在會堂裡點燃的燈火,意思是顯示:「匪黨聚集的地方不會點燃燈火。你應當走向你看到那些燈火的地方,大王。」
11. 正當阿闍世王從象乘上下來,開始步行時,世尊的光明就遍滿了他的全身。他立刻汗流滿身,他的衣服緊貼著他的身體,使他覺得似乎非脫下來不可。他想起自己所造的罪惡,心中生起大恐怖,因此他無法直接地走向世尊,而是拉著耆婆的手四處巡繞,好像來參觀精舍一樣,他說:「你建得很好,耆婆,你建得很好。」如此稱讚了精舍之後,他才漸漸走近會堂的門口。
為什麼他會問說:「世尊在那裡?」呢?有些人說:因為他不認識世尊。他們解釋說:在他小時候,他曾經與父親去見世尊;但是後來,由於結交了惡友,他殺害了自己的父親,派遣刺客(為提婆達多做事),放出護財象(那拉奇林Dhanapāla = Nāḷāgiri)(去攻擊佛陀),如此變成了大罪人,他不曾面對面地見過世尊,所以他不認得世尊。然而,這不是真正的理由。因為世尊在眾比丘的圍繞之下,坐在會堂的中央,就像眾星圍繞的滿月一般。世尊具足三十二種大丈夫相、八十種身體的美好,並且以六色的光明照亮了整個會堂,誰會不認得世尊呢?阿闍世王之所以如此問,只是顯示統治者的格調(issariyalīlā)而已。因為這就是王族貫有的特質:即使已經知道某件事情,他們仍然會好像不知道地那樣發問。而耆婆聽到這個問題之後,心裡想:「這個國王,自己就站在佛陀的面前,卻問說:『世尊在那裡?』這就好像站在地上的人問說:『大地在那裡?』或者好像抬頭仰望天空的人問說:『日月在那裡?』或者好像站在須彌山腳的人問說:『須彌山在那裡?』一樣。我來告訴他世尊是那一位。」於是耆婆向世尊恭敬問訊之後,說:「那位就是世尊,大王,」等等。
12. 當阿闍世王環視眾比丘時,無論他看向那裡,所有比丘都是安詳寂靜地坐著,沒有任何一位比丘在玩弄自己的手或腳,或者發出一聲咳嗽。也沒有任何一位比丘抬眼觀看站在世尊面前的阿闍世王和他的皇家隨從,以及全身打扮的那些宮女。所有比丘都一心只注視著世尊。
阿闍世王(見到)如此的安寧,心中生起信心。他一再地環視諸根平靜地坐著的比丘眾,就像一片清澈見底的湖水一般。於是他發出歡喜讚歎:「願我的兒子優陀夷跋陀王子也能享有這些比丘現在享有的安寧!」他這句話的意思是:「願他也能享有這群比丘現在享有的身語意安寧,以及行為的安寧。」他說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哦,願我的兒子出家(作比丘),並且能像這些比丘一樣安詳!」而是,由於見到比丘眾而引發信心之後,他想到自己的兒子。因為世間人常有的傾向是:當他們得到稀有的東西或看到美好的事物時,他們就會連想到自己所愛的親人或朋友。
再者,他講這句話乃是因為他擔憂自己的兒子,而希望兒子平和安詳。因為他想到:「我的兒子會問:『我的父親還這麼年輕;我的祖父到那裡去了?』如果別人告訴他說:『你的父親殺了你的祖父。』他的兒子可能會想:『那麼我也要殺死我的父親,我自己來統治國家!』由於擔憂自己的兒子,所以他講出這段話,希望他的兒子得到如此的平和安詳。雖然如此,可是後來他的兒子還是殺死了他。
在那個王朝,殺父的事件發生了五代。也就是:阿闍世殺死頻婆娑羅;優陀夷殺死阿闍世;優陀夷被自己的兒子摩訶文荼殺害;摩訶文荼被自己的兒子阿努律陀殺害;阿努律陀被自己的兒子那伽達沙殺害。那時人民感到憤怒,心裡想:「這些國王自己毀壞自己的血統,我們要他們有什麼用?」於是他們將那伽達沙殺掉。
大王,你的意念是否聽從情感的感召?
註:為什麼世尊如此說呢?據說在阿闍世王發出讚歎之前,世尊心裡想:「這個國王來到之後就沉默無言地站在這裡,他心裡在想什麼呢?」了知國王的心之後,世尊想:「由於國王無法與我交談,所以他環視比丘眾,因而想起了自己的兒子。我要開始與他談話。」因此,緊接在國王發出歡喜讚歎之後,世尊就說出上述這句話。這句話的意思是:「大王,正如雨水,降落在高地之後,就會向下流到平原;同樣地,在你環視比丘眾之後,你的愛就會趨向你的兒子。」
這時國王心裡想:「哦,佛陀的道德真是太崇高了!再也沒有人像我這樣曾經對世尊犯下嚴重的罪惡了:我殺害他的主要擁護者(頻婆娑羅王);我接受提婆達多的建議,派遣刺客去謀殺他;我放出那拉奇林大象去攻擊他;在我的支持下,提婆達多以岩石向他猛力投擲。對我這樣的一個罪人,佛陀甚至可以不要開口說話;然而他卻主動地先對我說話了。哦,世尊確實是具足五種堅固相(tādilakkhaṇa)之人!我絕不能放棄這樣的一位導師而去另外尋求其他導師。」他的內心充滿了歡喜,而對世尊說:「尊者,我愛我的兒子,」等等。
13. 世尊知道阿闍世王渴望提出問題,因此告訴他說:「儘管問吧,大王。」世尊邀請他發問,給予他一切知者的邀請,(暗示說):「儘管問吧,回答問題對我而言並不費事,我將回答你的任何問題。」這種邀請並非辟支佛、上首弟子或大弟子所能提出的,因為他們不會說:「儘管問吧。」而會說:「聽了你的問題之後,我會試著回答。」然而,諸佛會說:「儘管問吧。」來給予鬼神、國王、天神、沙門、婆羅門和修行者一切知者的邀請。
14. 阿闍世王因為世尊以一切知者的邀請允許他發問而感到歡喜,於是他提出可見的沙門果這個問題。此問題的要旨是:「是否可以指出就像各種世間技藝的可見成果,以及依靠這些技藝生活者所享受的可見成果那般可見的沙門果?」因此,就依靠那些技藝生活者而言,他提出了各種技藝。
「沙門果」(sāmaññaphala):就最終的意義而言,沙門指的是聖道,沙門果指的是聖果。正如經上說的:「諸比丘,什麼是沙門?沙門就是八聖道分,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什麼是沙門果?沙門果就是: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相應部》45:35/v.25)然而,阿闍世王不了解這些,因此,在以下的經文中,他問到有關奴隸與農夫的例子(所闡述的沙門果)。
15. 大王,你是否記得曾經問過其他沙門與婆羅門這個問題?
註:世尊並不直接回答問題,而是想到:「來到這裡的許多皇家大臣是外道諸師的弟子,如果我談到正面與負面的解釋,他們就會抱怨:『我們大王抱著熱切的渴望來到這裡;然而,從他一來到之後,喬達摩沙門就一直談論沙門之間的爭議與辯論。』如此他們就不會細心地聽法。但是,如果由阿闍世王來談論的話,他們就不敢抱怨了,因為他們必須服從國王;世間的人總是服從有權力者的話。因此,且讓我將(解釋外道六師教理的)這項任務交給國王。」於是世尊說:「大王,你是否記得曾經問過其他沙門與婆羅門這個問題?」來將此任務交給國王。
尊者,我不覺得麻煩
註:阿闍世王這句話的意思是:「當那些假裝有智慧的人在場時,說話是很麻煩的,因為他們會挑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的毛病。然而,在真正有智慧的人面前則不然,他們聽到別人所說的話之後,會稱讚說得正確的話;對於說得錯誤、違背義理與文句的話,他們則會糾正它、改正它。而再沒有能與世尊相比的真正智者了。」因此國王說:「尊者,當有世尊或與世尊同樣的人在場時,我不覺得麻煩。」
外道六師及其教理 回首頁
1. 布蘭迦葉的教理
17. 如果有人自己做……他並沒有造下罪惡
註:他解釋說:「即使有人內心存著『我正在造惡。』這種意念來做某件事情,他仍然沒有造下罪惡,他沒有惡業;(只是)眾生存著『我們正在造惡。』這樣的念頭而已。」
新疏:「內心存著『我正在造惡。』這種意念」:(布蘭迦葉)以這句話來顯示意念的存在,藉此,他說明:「即使故意做惡的人都沒有造下惡業,更不用說無心做惡的人了。」「他沒有造下惡業」因為人們不可能使原本就不存在的事物生起。因此他說:「沒有惡業。」
他的反對者提出這樣的問題來反駁他:「如果情況是如此(也就是:沒有惡業),那麼眾生為什麼會表現出罪惡的行為來?」為了要反駁這句話,布蘭迦葉說:「眾生(只是)心存這樣的念頭:『我們正在造惡。』而已,造作罪惡只是一種意念而已,沒有惡業。」
疏:(作為布蘭迦葉的道德虛無論的哲學基礎,)這指的是:「損傷、違害眾生等行為並沒有影響到自我,因為自我是恆常不變的。身體就跟木頭一樣,沒有心識,所以即使身體被毀壞了,仍然沒有罪惡產生。」
沒有(善或惡的)結果
註:「結果」(āgama)的意思是發生。在每一個例子中,他都否定惡或善的造作。
新疏:當一個人造作某事時,就在他的心流當中留下了能引生(相符的)結果之因素。因此,造業無效論的所有這些陳述斷言說:「沒有業,也沒有業的結果。」因為如果有業的結果,怎麼能說業沒有任何效力呢?
「在每一個例子中,他都否定惡或善的造作」:意思是他不解釋國王所問的可見沙門果。這項判斷的目的是指出他否定(業的)結果;因為否定業的人就是暗示著也否定結果。
2. 末伽梨瞿舍梨的教理
19. 眾生的煩惱沒有因或緣……不具備任何因緣,眾生就得以淨化
註:他藉著否定因緣這兩個字(因,hetu;緣,paccaya)來否定煩惱的真正原因,即:惡業等等;以及否定淨化的真正原因,即:善業等等。
沒有自決定、沒有他決定、也沒有個人決定。沒有能力、沒有活力、沒有個人力量、也沒有個人剛毅。
註:「自決定」(attakāra):就是眾生依照自己的判斷而造的業;由於此業,他得以生到天界、魔界、梵天界、證悟聲聞菩提、辟支菩提、或(佛的)一切知智。他否定這樣的事。
「他決定」(parakāra):乃是他人所給予的教誨與指導。依靠此指導,除了偉人(即菩薩)以外的一切人得以達到(各種善境)從人界的福樂到證悟阿羅漢果。他否定這種他人決定;如此,這個愚人打擊勝利者之輪。
新疏:偉人除外乃是因為在(證悟)出世間的成就方面,他們不依靠他人的指導;然而,在世間的成就方面仍要(依靠他人的指導),例如我們的菩薩得到阿羅拉與優陀羅的指導才證得五神通及世間的成就(《中部》26/i.163-66)。而且(註釋者的說明)指的是偉人在他們的最後一生之事;在此,也應當包括辟支菩薩在內,因為他們(的出世間成就)也不依靠(他人)決定。
「勝利者之輪」指的是解釋業報存在的佛教。他藉著否定業與業之效力的教理來打擊佛教。
註:「沒有個人決定」(purisakāra):他否定眾生藉以達到上述各種成就的個人決心。「沒有能力」(bala):他否定眾生能夠憑藉自己的能力而立足、激發自己的活力而達到成就。「活力」、「個人力量」、「個人剛毅」這三詞都是個人決定的同義詞。它們分開來說是為了否定下列這句聲稱:「透過我們自己的活力、個人力量與個人剛毅才獲得這項成就。」
一切有情、一切眾生、一切生物、一切靈魂都是無助、無力、無能的
註:「一切有情」(sabbe sattā):他將駱駝、牛、驢等都包括無遺。「一切眾生」(sabbe pāṇā):他是指有一根或二根的眾生。「一切生物」(sabbe bhūtā):這是指由卵生或胎生的生物。「一切靈魂」(sabbe jīvā):這是指稻米、大麥、麥等,因為它們會生長,所以他認為它們有靈魂。「都是無助、無力、無能的」:他們沒有自制力、力量、能力。
他們透過命運、環境與本質而進行轉變,在六類人當中經歷苦樂
新疏:命運(niyati)就是宿命(niyamanā),也就是說:投生處所、社會地位、束縛、解脫都已固定,由事情發生的必要順序所決定;就像用一條切不斷的線所貫穿起來的一串牢不可破的珠寶一樣。
註:「環境」(sangati):是指到處地來往於六類人之中。
新疏:遭遇全部歷程,投生為六類人當中相關的人,在各種不同的生命當中到處來往。
註:「本質」(bhāva):內在本質(sabhāva)。
疏:他堅持說整個世界藉著它自己的內在本質而沒有因或緣地,自動地、獨自地以各種方式轉變,就好像刺的尖銳性、蘋果的圓形、以及各種動物與鳥的形狀一般。
註:藉著這整段話,末伽梨瞿舍梨說明:「(所有眾生)如此由於命運、環境與本質而轉變與造成差異。註定會發生的就會發生;註定不會發生的就不會發生。」
「六類人」(cha abhijāti):他們滯留在六類人當中經歷樂與苦。他顯示沒有其他樂與苦的生存界。
(眾生)有一百四十萬種主要的起源、六千種(其他起源)及六百種(其他起源)。有五百種業、五種業、三種業、滿業及半業。有六十二道、六十二小劫
註:主要的起源(vonipamukha)是最高的起源。
新疏:在人類當中,剎帝利與婆羅門等是主要的起源;在動物當中,獅子與老虎等是主要的起源。
註:「五百種業」:他解釋單憑推論而想出來的無意義見解。對於「五種業」、「三種業」等等也是同樣的情況。但是有的人說:「他依據五根而說五種業;依據身(口、意)業而說三種業。」
疏:「單憑推論」:因為理性論者缺乏〔掌握真實意義的〕方法,他們想像自己內心的解釋是真實的;由於執著它們,他們執取自己理性見解的假設。因此智者不需要個別地探討他們的每一項見解。
註:「滿業及半業」:在此,他的理論是:身業和語業為滿業,意業為半業。
疏:他的理論是:因為前兩者比較粗,所以是滿業;而意業比較細,所以是半業。
註:「六十二道」:〔由於不了解正確的語言,〕他把六十二道說成dvaṭṭhipaṭipadā,〔而正確的應當是〕dvāsaṭṭhipaṭipadā。
「六十二小劫」:(antarakappā):在一個大劫裡有六十四個小劫;但是由於他不了解這兩種劫,所以他說(有六十二小劫)。
六類人(cha
abhijātiyo)
註:他宣稱有六類人,即:黑、藍、紅、黃、白與究竟白。
(1)註:黑類(kaṇhābhijāti)包括屠夫、獵人、漁夫、盜賊、劊子手、典獄者以及其他從事殘酷行業之人。
(2)註:藍類(nīlābhijāti)由比丘所組成;他說:因為比丘將刺投入四種資具(袈裟、食物、住處和醫藥)而受用之。他自己的經典中說:「比丘有多刺的行為。」(bhikkhū kaṇṭakavuttikā)。
疏:這裡的「比丘」指的是佛教的比丘。他說:「他們將刺投入四種資具而使用」意思是他們以貪愛和慾望來使用資具。
新疏:這裡的「刺」指貪愛和慾望;而「將刺投入」指被貪愛和慾望束縛而使用資具。
疏:為什麼他如此說呢?他立下錯誤的假設說比丘使用最上等的資具;因此,即使比丘使用經由正當途徑取得的資具,他還是說:「他們將刺投入資具而使用。」因為這與邪命外道的教義相違背。
註:或者,他認為有些出家人有多刺的行為。
疏:也就是說有些〔佛教以外的〕出家人特別沉迷於自我折磨的苦行,如此,他們就好像是活在許多刺之上。
(3)註:紅類(lohitābhijāti)由只穿一衣的尼乾陀(耆那教徒)所組成;因為這些人比前述的兩種人更清淨。
疏:因為他們持守斷食和不洗身的戒,所以他們更清淨。
(4)註:黃類(haliddābhijāti)由裸體外道的白衣在家人所組成。如此,他甚至把自己的在家信眾排在尼乾陀教徒之上。
疏:裸體外道(acelakā)就是邪命外道。根據邪命外道的理論,因為他們的心比較清淨,所以他們比較高級。
(5)註:白類(sukkābhijāti)包括邪命外道的男女教徒。他說:他們比前述的四類更清淨。
(6)註:究竟白類(paramasukkābhijāti)由難陀瓦加、提沙桑提加與末伽梨瞿舍梨所組成。因為他們最清淨。
疏:因為他們已經達到邪命外道特殊修行的巔峰,所以他們是究竟白類,他們比尼乾陀、邪命外道以及他們的在家信眾更清淨。
八個人生時期(aṭṭha
purisabhūmiyo)
註:他宣稱人生有八個時期:(1)軟弱期;(2)遊戲期;(3)學走期;(4)直立期;(5)訓練期;(6)沙門期;(7)勝利期;(8)衰老期。
(1)軟弱期(mandabhūmi):這是出生之後七天內的時期;因為眾生剛出胎之時是軟弱與遲鈍的。
(2)遊戲期(khiddabhūmi):從惡趣來投生的人通常哭泣、號啕;從善趣來投生的人會回憶起前世,因而歡笑。
(3)學走期(padavīmaṁsabhūmi):在此時期,小孩抓著父母的手或腳、或床、或椅而開始學走路。
(4)直立期(ujugatabhūmi):在此時期,小孩已能用腳走路。
(5)訓練期(sekhabhūmi):這是訓練某一種技藝的時期。
(6)沙門期(samaṇabhūmi):這是捨離在家生活而出家(為沙門)的時期。
(7)勝利期(jinabhūmi):這是服事一位導師之後,獲得知識的時期。
(8)衰老期(pannabhūmi):這是比丘、衰老者、勝利者、沉默不言者、無所得沙門的時期。
疏:「勝利者」(jina)乃是已經年老(jiṇṇā)、因年老而力衰的人,或克服修行上的障礙而安住的人。他說,如此的人不對任何人說話,即使連自己的教理也不談;因此他「沉默不言」。然而,有人解釋說:即使他受到別人侮辱,乃至被罵為駱駝等,他也不說任何話(反擊),只是耐心地忍受。
他「無所得」(alābhi),因為他不藉著自己的誓言而獲得物品;經上說到:「他不從鍋口接受食物。」(《中部》51/i.342)。因此,由於被飢餓與虛弱所擊敗,最後他平躺了下來。這就是所謂的衰老期的沙門。
三十六塵界、七個有想有情界、七個無想有情界、七種節生植物、七種神、七種人、七種餓鬼、七大湖
註:「三十六塵界」:灰塵積聚的地方。他的意思是指手背、腳底等處。「七個有想有情界」:他指的是駱駝、牛、驢、羊、家畜、鹿和水牛。「七個無想有情界」:他指的是穀、米、大麥、小麥、粟、豆和加堵沙(kadrūsaka)。「七種節生植物」:從節生長出來的植物;他指的是甘蔗、竹、蘆葦等。
「七種神、七種人」:神有許多種,他卻說七種。人也是一樣,有無數種人,他卻說七種人。「七種餓鬼」(pisācā):餓鬼有許多種,他卻說七種。「七大湖」:他指的是鈍角湖(Kaṇṇamuṇḍa)、造車湖(Rathakāra)、無熱惱湖(Anotatta)、獅子崖湖(Sīhappapāta)、六牙湖(Chaddanta)、曼陀吉尼湖(Mandākiṇī)及郭公湖(Kuṇāladaha)。
八百四十萬大劫
註:他敘述一個大劫的時間是:每隔一百年用吉祥草葉的尖端從一個大湖中取走一滴水,如此一直到將大湖的水取乾,所經歷時間的七倍,就是一個大劫的時間。他的理論主張八百四十萬個如此的大劫過去之後,愚者與智者都同樣息滅一切苦。他說:智者不能在這段時間之前淨化自己;愚者在這段時間之後就不復存在。
疏:為什麼呢?因為眾生(在輪迴中)流轉的時間期限是固定的。
藉著道德修養、或持戒等等
註:藉著裸體外道或其他宗教的道德修養。「持戒」也應以同樣的方式去理解。對於──自認為是智者的人「將能使未成熟的業成熟」或「去除已成熟而現起的業」意思是他將能提早淨化自己。以及自認為是愚者的人在所說的(輪迴的)期限之後還會繼續輪迴──這兩件事,「那是不可能的」意思是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發生。「輪迴的界限是固定的,既不能縮短,也不能延長。」:對智者而言輪迴不能縮短;對愚者而言,輪迴不能延長。
3.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的教理
22. 沒有布施、沒有供養、沒有解脫、沒有善惡業的果報。
註:他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沒有布施、供養和解脫的果報。
沒有今生、沒有來生
註:對於活在來生的人而言,今生是不存在的;對於活在今生的人而言,來生是不存在的。他顯示:一切都在當處滅絕。
疏:對於活在來生的人,沒有由於業而有的今生;對於活在今生的人,沒有由於業而有的來生。
「一切都在當處滅絕」:無論他們活在那一界、那一種起源等等,他們就在該處滅絕;他們滅盡而不會(在其他處)生起。
沒有父親、沒有母親
註: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以善行或惡行對待父母親沒有果報存在。
沒有投生的眾生(sattā
opapātikā)
註:他說眾生死亡之後不再(以投生的方式)出現。
疏:他顯示:「眾生的生起完全和水泡的生起一樣;他們並不是先在別處死亡之後,才生到此處來的。」
(他身體中的)地回歸及併入(外在的)地體
註:內在的地界(回歸及併入)外在的地界。其餘的諸界也是同樣的情況。
疏:外在地體的一部份藉著成為眾生內在(身體)的一部份而塑造成眾生。現在,就像構成壺罐等的土一般,該地界回歸與併入外在的地體,二者完全合一、不可分辨。
「其餘的諸界也是同樣的情況」:意思是,就像水從海洋中蒸發而變成雲,然後變成雨水降落而回歸及併入海洋一般;又像閃電的光芒來自日光,然後又回歸及併入日光一般;也像一陣風從整團的空氣中分離出來,然後又回歸及併入空氣一般(──身體的各種界也是同樣的情況)。這是此理論家的意旨。
他的感官歸於虛空
註:包括心在內的六根歸入虛空。
他的慈善布施終歸於灰燼
註:意思是:「他所布施的物品,如禮物、榮譽等全部歸於灰燼;它們不會進一步產生果報。」
布施是愚人的教理
註:他表示:「愚人教導布施,而智者不然;愚人布施,智者接受。」
綜觀三派教理 回首頁
註:在這三派之中,布蘭迦葉主張「如此做沒有罪惡」乃是否定業〔因為他的教理是造業無效論〕。阿耆多主張「身壞命終之後眾生滅絕」乃是否定業的果報〔因為他完全否定未來的再生起〕。末伽梨主張「沒有因等等」乃是否定業與果兩者。
疏:(他否定兩者,)因為藉著完全否定因,果也就被否定了。當他主張「不具備任何因緣,眾生就生起煩惱和得以淨化」時,他這種煩惱與淨化無因緣的主張否定了業,同時也否定了果;因此他否定業與果兩者。
註:否定了業也就否定了果〔因為沒有業就沒有果〕;否定了果也就否定了業〔因為沒有果的話,業就是無效的。〕因此這三派思想家藉著否定(業與果)兩者,實際上就是信奉無因論(ahetukavāda)、無作用論(akiriyavāda)及道德虛無論(natthikavāda)。
疏:雖然在經中由於這三派理論家個別解釋自己的見解而分成三派,但是他們都否定(業與果)兩者;由於否定兩者,因此他們都信奉無因論等。就道德虛無論者而言,他藉著否定結果而信奉斷滅論;而且實際上就是藉著否定業而宣揚造業無作用論,以及藉著否定兩者而宣揚無因論。其餘兩派也是同樣的情況。
註:當人們接受這些理論,而坐在他們的日間住處或夜間住處背誦及研究它們時,邪念就會以(這三種見解之一)為對象而建立起來:「沒有造作惡業。」或「沒有因或緣。」或「死後斷滅。」於是心變得專一,速行心接連地生起。在第一個速行心時,這些人還可救;在第二個速行心等時也還可救,但是到了第七個速行心時,即使連佛陀也無法挽救他們;他們的邪見已無法挽回。
有人可能會信奉這三種見解之中的一種、兩種、或三種;然而,無論是信奉一、二或三種見解,他就是信奉固定結果的邪見,這會障礙他投生天界之道及解脫之道;下一生他不可能投生天界,更不用說證得解脫了。這個眾生已經成為輪迴中的木樁、土地的看守者。一般而言,如此的人無法解脫輪迴。
因此具備洞察力者,
期盼獲得心靈提昇,
當遠離此有害之人;
正如遠離毒蛇一般。
疏:「邪念建立起來」(micchāsati santiṭṭhati):邪念就是與此理論有關的欲望,建立起來的就是這種欲望。因為經由口頭傳授之後,弟子最初只理解了此邪見的大體意義「如此做沒有罪惡」等等。然後他以各種理由仔細地思考此意義,直到此意義猶如具有實在形體般地令他的心信服。熟悉這樣的邪見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他變成反射性地認同此邪見,心裡想「這是真實的。」當他透過反射性認同來接受此邪見為真實的,並且習慣性地一再沉迷與培養此邪見時,邪思惟就會將欲望導向此邪見,邪精進又加強此欲望,於是他就會認定事物具有某種本質,而事實上事物並不具有這種本質。因此,與該理論相關的欲望就稱為邪念。
「心變得專一」:在得到像尋心所等這些特定的助緣之後,心變得穩定安住在它的對象;它去除散亂而變得專一,猶如進入安止一般。「邪定」(micchāsamādhi)乃是在「心」的前提下並談到的,因為在透過特定助緣而增強有力之後,那樣的定就會執行其作用,而不正當地將心專注在它的對象,就像神箭手等的例子一樣。
「速行心接連地生起」(javanāni
javanti):在先前的許多組速行心以那種方式發生了許多次之後,〔堅信邪見是真實的〕最後這一組七個速行心就接連地生起。「在第一個速行心時,這些人還可救」等等:這只是顯示事物的內在本質而已,因為在那一刻已經沒有人能夠挽救他們。
新疏:(沒有人能夠挽救他們)因為當他們處在那些速行心的狀態時,要避免第七個速行心生起是不可能的。心路過程的發生是如此的快速,因此(在那時)要藉著教誨與指導來挽救他們是不可能的,所以註釋者說:「即使連佛陀也無法挽救他們。」
疏:「有人可能會信奉這三種見解之中的一種」等等:有人執著並且習慣性地沉迷於單一種邪見、信奉單一種邪見;有人執著並且習慣性地沉迷於二種或三種邪見、信奉二種或三種邪見。藉著這些話,註釋者顯示前面解釋這些邪見都是否定(業與果)兩者的所有討論都只是初步的開端而已;當(對某一種邪見的信奉)引導人達到邪性決定的階段時,該邪見並不與其他邪見合併在一起。由於此邪見是透過它本身的種種助緣和合而產生的,因此它不與(其他邪見)同時產生,就像(禪那等)卓越的成就不會取各種不同對象同時產生一樣。
「然而,無論是信奉一、二或三種見解」:藉著這句話,註釋者顯示這三種邪見都具有同樣的力量,能產生相同的結果〔那就是,它們會障礙投生天界(以及證悟聖道)〕;因此,雖然這三種邪見分別地在單一個人身上生起,但是當一種邪見產生果報時,另外兩種則會助長該邪見的力量。
「輪迴中的木樁」:這是一句需要解釋的話(neyyattha.未了義),而不是意思很清楚的話(nītattha.了義)。因此在(《中部》的註釋《破除疑障》(Papañcasūdanī)中說到:「(由於邪見的緣故,)他未來的固定結果是只限於一生(來生),或者是也涉及以後的生生世世?未來固定的結果只限於一生(來生);但是因為他一再地沉迷於那種邪見,所以在以後的生命當中,他也會再認同同樣的邪見。」(《中部》3:85)由於不善業是軟弱無力的,不像善業那樣強而有力,所以說邪見的固定結果只限於(來生)一生而已;否則,邪性決定就會像正性決定一樣,是絕對無法更改的,然而,事實上邪性決定並非絕對無法更改的。
問:若是如此,那麼「輪迴中的木樁」這句話如此能運用(於信奉如此邪見的人)呢?
答:由於他習慣性地沉迷(於那種邪見),正如《增支部》(Aṅguttara Nikāya 7:15/iv.11)中所說的:「愚痴的人即使只墮落一次也是真正的墮落。」這裡「輪迴中的木樁」也是用同樣的表達方式。因為他基於某些情況而信奉該邪見;於是,無可否認地,有時基於相反的情況,他可能會設法脫離該邪見。所以,註釋裡才說:「一般而言,如此的人無法解脫輪迴。」
新疏:(「這個眾生已經成為輪迴中的木樁」)這句話是未了義的話,而不是了義的話,因為這句話的含義需要如此解釋:「他成為『輪迴中的木樁』,因為一般而言,如此的人無法解脫輪迴,由於他習慣性地沉迷於某種邪見,所以在以後的生命當中,他也會再認同同樣的邪見。」然而,必須補充說明的是,他並不是成為邪性決定絕對無法更改那種意思的「輪迴中的木樁」。
4. 波拘陀迦旃延的教理
未經製作、未經形成(akaṭā
akaṭavidhā)
疏:「未經製作」意思是它們並非由相同性質或不同性質的任何原因所製作、形成。
註:「未經形成」意思是並沒有任何人下令做成它們。
疏:也就是說,它們的形成不經任何命令或規則。藉著(「未經製作」和「未經形成」)這兩個詞,他顯示這七身不是由世間的任何因或緣所造成。
未經創造的、沒有創造者(animmitā
animmātā)
註:「未經創造」:並非被神通力所創造。
疏:並非由成就神變智的天神(deva)的神通力所創造;也不是由造物天神(issara.自在天)等的神通力所創造。
不生、穩定如山峰、堅立如柱的
疏:「不生」(vañjā):它們不會有結果,就像不孕的家畜、不孕的棕櫚樹等一般,它們不會產生任何事物。藉著這句話,他否認了地身等會產生色塵等的這個概念,因為在他的理論中,色塵、聲音等是不靠地身等而獨立產生的。
「穩定如山峰」(kūṭaṭṭhā):這句話的用意是這些不靠任何事物製造,而且它們本身也不製造任何事物,就像山峰一樣。
「堅立如柱」(esikaṭṭhāyiṭṭhitā):(他堅持說)當有人講:「芽等是從種子長出來的。」這句話時,從種子長出來的芽已經存在了,而非之前不存在的東西;否則,推論就會變成事物是從(完全)不同的事物產生的。〔關於這七身也是同樣的道理。〕
它們不變化、不更改(na
iñjanti na vipariṇāmenti)
註:由於它們是穩固的、堅立如柱的,所以「它們不變化」,意思就是不會變質;以及「不更改」,意思就是不會捨棄它們原本的性質。
不互相障礙(na
aññamaññaṁ byābādhenti)
疏:因為它們的性質不可變,所以它們不會互相障礙;如果它們能夠變質,它們就會互相障礙。同樣地,因為它們無法互相幫助,所以它們不互相助長。書中要說明這一點,所以說:「它們不能造成彼此苦、或樂」等等。
地身等等
註:地身就是地本身,或者地的聚集〔因為地是身體的一部份〕。
沒有殺生者等等
註:就像有人用劍砍一堆豆子,劍進入豆子之間;同樣地,(在顯而易見的殺生行為當中)劍進入七身之間的空間、空隙,因此他說:(當一個人心裡想)「我正在殺害他的生命」時,那純粹只是想法而已。
疏:由於七身是恆常不變的,所以沒有所謂殺生及令別人殺生的事;因此沒有殺生者,也沒有令別人殺生者。由於這七身是不可破壞的,因此在究竟的意義來說,沒有殺生,也沒有令別人殺生等等。
5. 尼乾陀若提子的教理
尼乾陀教徒禁絕涉及一切水等等
註:「禁絕涉及一切水」(sabbavārivārito):他拒絕使用一切冷水。據說他認為冷水中有眾生,所以不使用冷水。
疏:「他自然免離一切罪惡」(sabbavāriyutto):他自然具備免離一切種(罪惡)的特質。
「他透過免離一切罪惡而淨化」(sabbavāridhuto):他藉著免離一切罪惡而抖落罪惡,具備磨損(罪惡)的特質。
「他被免離一切罪惡所充滿」(sabbavāriphuṭo):他被免離一切罪惡所充滿,其特質是透過滅除八種業所證得的解脫而摧毀業。
他被稱為自圓、自制、自立的無結者
註:「自圓」(gatatto):心達到顛峰的人。
疏:他的心透過證得解脫而達到最高的領域。
註:「自制」(yatatto):已經征服自己的心之人。
疏:因為在身等諸根當中沒有需要被征服的,所以他已征服自己的心。
註:「自立」(ṭhitatto):心已經安立的人。他的教理中有一部份與佛陀的教法相符,但是因為他的理論不純淨,所以全部被認定為(邪)見。
疏:與佛陀的教法相符的部份是必須免離罪惡;不純淨的理論是他主張「有靈魂存在,靈魂可能是恆常的,可能是無常的」等等。
「全部被認定為(邪)見」:他透過思惟而認定的所有觀點──業、本質、分析等(教理)──都被認定為邪見。
6. 薩若毘耶梨弗的教理
註:薩若毘的教理在《梵網經》(Brahmajāla Sutta)的註釋裡,談到「永遠模稜兩可的教理」一章中有所解釋。
第一種可見的沙門果
33. 因此,尊者,我請問世尊
註:這句話的含義是:「正如壓榨沙子無法得到油一般,我無法從六派導師的教理中得到任何真義,因此我請問世尊。」
34. 且讓我剃除鬚髮
註:這句話顯示奴隸熱切想出家背後的心態是:「如果我實行布施的話,盡我一生之力行布施,也達不到國王一天所行布施的百分之一。〔因此我應當出家。〕
滿足於最簡單的飲食與住所
註:摒棄以不正當的方法尋求(飲食與住所)之後,他透過最高的捨離心而知足。
疏:另一種解釋法是:由於他已安住於崇高的境界,他最大、最高的需求只是飲食與住所而已;除此之外,他不尋求或期望其他任何物質。
樂於獨住
註:他樂於三種獨住,即:「身獨住(kāyaviveka)是針對身體方面獨住之人而言;心獨住(cittaviveka)是針對樂於出離的人、達到最高淨化的人而言;究竟獨住(upadhiviveka)是針對無所得的人、超越諸行的人而言。」(《中部.大義釋》26)捨棄人群之後,身體方面得以獨住;捨棄煩惱群之後,心得以藉著八定而獨住;證悟涅槃、進入果定或滅盡定之後,得以究竟獨住。
更殊勝的沙門果 回首頁
40. 大王,諦聽及謹慎注意
註:在此,「諦聽」一詞是避開耳根方面散亂的命令;「謹慎注意」則是加強注意、避開意根方面散亂的命令。前者是為了避免對文詞的曲解;後者是為了避免對義理的曲解。藉著前者,佛陀吩咐聽者聆聽佛法;藉著後者,吩咐聽者將所聆聽的法謹記在心、仔細思惟法等等。藉著前者,佛陀顯示:「此法具足文詞(sabyañjano),是故應當聽聞。」藉著後者,佛陀顯示:「此法具足義理(sāttho),是故應當謹慎注意。」或者「謹慎」(sādhukaṁ)一詞可以與(「諦聽」及「注意」)兩詞合在一起解釋,如下:「由於此法在教義方面深奧、在教法方面深奧,因此應當謹慎諦聽;由於此法在義理方面深奧、在通達方面深奧,因此應當謹慎注意。」
41. 在此,大王,如來出現於世間
註:有三種世間,即:器世間、有情世間、行世間。這裡的世間是指有情世間而言。當如來出現於有情世間時,他不會出生於天界或梵天界,而只會出生於人界。他不會出生於人界裡的其他世界系,而只會出現於此世界。他不會出生於此世界的其他地方,而只會出生於中區(北印度)。不只如來是如此,辟支佛、上首弟子、八十大弟子、諸佛之父母、轉輪聖王、以及其他卓越的婆羅門與居士也都只出生於此地。
從如來(在證悟的前夕)接受善生(sujātā)供養的蜂蜜與奶飯起,到他證悟阿羅漢道這段時間,稱為如來「正在出現」;在他證悟阿羅漢果時,稱為「已經出現」。或者從他出家、或從(他從)兜率天(下降)、或從他在燃燈佛(Buddha Dīpankara)足下(發成佛之願)起,到他證悟阿羅漢道,這段時間稱為「正在出現」;證悟阿羅漢果時稱為「已經出現」。在此,「出現」一詞指的是第一種說法中所解釋的已經出現的情況。因此,這段經文的意思是:「如來已經出現於世間。」
他以親身現證的智慧了解
註:這句話排除了推理的智慧等。
疏:推理的智慧、相似的、暗示的意義等都被排除了,因為諸佛世尊只有一種智慧,他們透過無礙慧根的作用,而以直接的認知來明瞭一切。
這個有諸天、諸魔、諸梵天等的世間
註:在這裡,「諸天」一詞包括欲界天裡下面五層天的天神。「(有)諸魔」一詞包括欲界第六層天的天神。「(有)諸梵天」一詞包括梵天的隨從等。「有諸沙門與婆羅門」包括敵視、反對佛教的沙門與婆羅門,以及真正平息與排除諸惡的沙門與羅婆門。「這個世代」一詞包括有情世間。「有諸王與人」一詞包括傳統的天(即國王)及其餘的人。如此,這裡前三個(形容世間的)詞包括了有情世間及物質世界;「世代」及它的兩個形容詞則只包括有情世間而已。
另一種解釋法:談到「有諸天」就包括了無色界的天神;談到「(有)諸魔」就包括了六層欲界天的天神;談到「(有)諸梵天」就包括色界梵天的天神;談到「有諸沙門與婆羅門(的世代)」等就包括有傳統的天(國王)及四種姓階級的人間,或者包括其餘的所有世間眾生。
再者,藉著「有諸天」一詞,佛陀談到他明瞭整個世間,以最高的一界來劃分。〔因為在五趣當中,天趣的諸界是最好的。其中,由於無色界具有特別的素質,因此更為殊勝;這些素質例如:免除煩惱之苦,具有安寧、崇高、不動的住處,以及壽命極長。〕然而,有些人可能會想:「魔王的神通廣大──他是六層欲界天的統治者。難道佛陀也明瞭他嗎?」為了去除這些人的疑惑,佛陀說:「(有)諸魔」。另外有些人可能會想:「梵天的神通非常廣大,他能夠以十指放光遍照一萬個世界系,而且他享用無比的禪那之樂。難道佛陀也明瞭他嗎?」為了去除他們的疑惑,佛陀說:「(有)諸梵天」。然後有些人會想:「有許多反對佛教的沙門與婆羅門,難道佛陀也明瞭他們嗎?」為了去除他們的疑惑,佛陀說:「有諸沙門與婆羅門」。如此顯示他明瞭最殊勝的階層之後,佛陀說:「有諸王與人」顯示他也明瞭其餘的世間眾生,藉著其中最殊勝的份子即傳統之天(諸王)及其餘人類來劃分。這是藉著心態來陳述用詞的順序。〔藉著他人的內心傾向。〕
然而,古代的大德說「有諸天」一詞是指天神以及世間的其餘眾生;「(有)諸魔」是指諸魔以及世間的其餘眾生;「(有)諸梵天」是指梵天以及世間的其餘眾生。因此,佛陀以這三詞來包含三界的一切眾生,而用三個不同的觀點來描述。然後以接下來的兩個詞──「這個有諸沙門與婆羅門、諸王與人的世代」──再次涵蓋整個世間。如此,就以這五個詞,由不同的觀點來描述整個三界。
他說法初善、中善、後善等
註:基於對眾生的大悲心,世尊甚至離開無比的獨住之樂,而為眾生說法。無論他說的多或少,所說的法都具有初善、中善、後善等特質。他使所說的法在開始、中間與結尾都完美、悅耳、無瑕。
(個別)一次說法(desanā)有開始、中間與結尾,而整期教化(sāsana)也有開始、中間與結尾。就一次說法而言,即使在一首四行偈中亦然:第一行是開始,接著的兩行是中間,最後一行是結尾。在講述單一組含義的經中,前言是開始,「世尊如此開示之後」這一句是結尾,這兩者之間的部份是中間。在講述多組含義的經中,第一組含義是開始,最後一組含義是結尾,二者之間的──無論是一、二或多組含義──是中間。
就一期教化而言,戒、定、慧是開始,因為經上如此說:「什麼是善法的起點呢?那就是淨戒與正見。」(《相應部》47:3/V.421)然後經上又說:「諸比丘,如來證悟中道。」(《相應部》56:11/V.421)因此聖道是中間。而結尾是聖果與涅槃。在下列這段經文中,聖果被稱為結尾:「這是梵行生活的目標、實質、結尾──(不可動搖的心解脫)」。(《中部》29/i.197)而在下面這段經文中,涅槃被稱為結尾:「賢友毗舍佉,梵行生活導入涅槃;涅槃是梵行的最終歸趣,涅槃是梵行的結尾
。」(《中部》44/i.304)
此處經文所說的是指說法的開始、中間、結尾,因為當世尊說法時,一開始他先說持戒,中間說行道,結尾說涅槃,因此經上說:「他說法初善、中善、後善。」
其他法師說法時也以如此的方式說。
具足義理與辭句(sātthaṁ
sabyañjanaṁ)
註:有些人說法時談論有關食物、男人、女人等的解釋,如此不是「具足義理」的說法;世尊捨棄那些說法,而教導四念處等法,因此他說法「具足義理」。
有些人說法時缺乏各種完整的辭句,或各種發音混淆,如此稱為「不具足辭句」的說法;世尊說法時辭句完整,各種發音分明不含糊,因此他說法「具足辭句」。
徹底圓滿與清淨
註:它是「徹底圓滿」的,因為在它之中沒有什麼欠缺,也沒有什麼過度,不需增加,也不需減少。它是「清淨」的,因為沒有腐敗。如果有人存著想要獲得名譽及供養的心來說法,那麼他的說法是不清淨的。而世尊說法全然不在意世間的得失,他以慈悲柔和的心,充滿為他人福利(之願),以令他人解脫的心而說法。〔即內心存著使他人從一切煩惱與輪迴之苦中超脫出來的悲願。〕因此他教導清淨的法。
他顯示梵行
註:(諸經文中)提到的「梵行」(brahmacariya)有下列的含義:布施、服務、五戒、四無量心、不行淫、滿足於自己的結婚伴侶、精進、布薩戒、聖道及整個教法。在此,它是指教法而言。所以,應當如此理解這段經文:「他說法初善等……徹底圓滿與清淨。他如此說法以顯示梵行,即包含(戒、定、慧)三學的整個教法。」
42. 平民、或平民之子
註:為什麼佛陀先提到平民呢?因為他們謙卑,而且佔大多數。一般而言,由剎地利家族出家的人會因為家世顯赫而感到驕傲;由婆羅門家族出家的人會因為博學咒文而感到驕傲;由賤種出家的人會因為出身低微而無法妥善自立;而耕田的平民小孩腋下流著汗水、背上的汗跡閃閃發亮,他們沒有前述的那些驕傲,因此是謙卑、不驕慢的。他們出家後不會傲慢自大,而會盡全力學習佛陀的所有教導,修行觀禪,證悟阿羅漢果。而且,由其他種姓家庭捨俗出家者的人數不多,由平民家庭出家者則人數很多。因此,由於平民很謙卑而且佔多數,所佛陀先提到他們。
在家生活是狹隘的、是塵擾之途
註:即使只是一對夫婦,住在廣長一百由旬的莊園裡,六十腕尺的房子中,在家生活仍然是狹隘的。這是因為在家生活涉及障礙(如貪慾等)與妨礙(如田園、土地等)。這是「塵擾之途」,即貪慾等塵勞生起之路。
出家則有如曠野一般開闊
註:出家生活有如曠野是因為不受障礙。即使出家人住在門窗關閉、屋頂覆蓋的尖頂小屋、珠寶裝飾的宮殿、或天宮等,他仍然是不受障礙、無拘無束的。再者,在家生活是狹隘的,因為行善的機會少。那是塵擾之途,就像不受管制的土堆,是塵土聚集的地方,意即煩惱之塵聚集之處。出家猶如曠野,因為它給與人盡情行善的機會。
徹底圓滿、徹底清淨的梵行生活
註:三學的梵行生活是「徹底圓滿」的,因為它要被履行到心的最後一刻,要被保持得完整無缺,即使只有一天的時間。它是「徹底清淨」的,因為它要被履行到心的最後一刻,要被保持得絲毫不受煩惱污染,即使只有一天的時間。
44. 他擁有良好的身語業,活命清淨
註:提到「正當的行為與行處」時,良好的身語業已經被包括在內了;然而,活命清淨戒並不存在於天空或樹梢,而存在於身體與言語的門戶。因此,為了顯示它生起的門戶,所以經文中說:「他擁有良好的身語業」。由於他擁有這些,所以他的活命是清淨的。
45-62. (關於比丘所守戒條的解釋,註釋者指示讀者參閱《梵網經註釋》中戒律的章節。那裡的部份評語已合併入英文翻譯本身之中,更詳細的敘述請參見The All- Embracing Net of Views,
pp. 118-25。
63. (他)見到自己在持戒的各方面都沒有危險
註:他在自己的各方面見不到任何由於不持戒而生起的危險。為什麼呢?因為他持戒,所以不會遇到任何起源於不持戒的危險。
他內心體驗到無罪的快樂(anavajjasukha)
註:他內心體驗到一種無罪、無瑕、健全的身心快樂,伴隨著以戒為近因的無悔、愉悅、欣喜與輕安等法。
守護諸根(indriyasaṁvara) 回首頁
64. 眼見到物體之後
註:在諸經中,「眼」(cakkhu)這一字有下列這些含義:
(1)
佛眼。如所說:「他以佛眼觀世界」(《中部》26/i.169);
(2)
世界眼;一切知智。如所說:「登上法殿,大智者!世界眼!」(《中部》26/i.168);
(3)
法眼;前三聖道的智慧。如所說:「他的心中生起無垢、無瑕的法眼。」(《中部》74/i.501);
(4)
慧眼;宿命智〔以及漏盡智〕。如所說:「眼生起了,智生起了。」(Vin.i.11);
(5)
天眼(如《沙門果經》第97節);
(6)
肉眼。如所說:「依靠眼根與色塵,眼識得以生起。」(《中部》18/i.111)。
在此,傳統上有感官意思的「眼」用來指眼識而言。因此,上述那句經文的意思是:「以眼識看見物體之後」。關於其他字需要解說的部份在《清淨道論》第一章.第53-59節中都已解說。
他內心感受到無缺點的快樂(abyāsekasukha)
註:他感受到增上心的清淨快樂(adhicittasukha增上心樂)。這種樂是無瑕疵、無摻雜的,因為它沒有煩惱污垢。
疏:說「增上心樂」是因為當根律儀戒被持守得完全清淨時,主要的惡法〔五蓋〕就會消失。結果很容易就能致力於得到增上定。
正念與正知(sati-sampajañña)
I. 向前行與返回時的正知
65. 向前行與返回時
註:在此「向前行」是前進,「返回」是回轉,在所有四種姿勢中都有這兩者。首先,在行走的時候,「向前行」是使身體向前進;「返回」是使身體回轉。在站立的時候,使身體彎向前地站著是「向前行」;使身體仰向後地站著是「返回」。在坐著的時候,移向座位前面部份地坐著是「向前行」;移向座位後面部份地坐著是「返回」。在躺臥的時候也以同樣的方法解釋〔即:躺臥時身體移向前與移向後〕。
比丘都以正知而行(sampajānakārī
hoti)
註:他以正知做一切事務,或者他練習正知。由於他在向前行等各種情況下練習正知,因此他從未欠缺正知。
疏:正知(sampajāno)的人乃是〔以各種方式〕廣泛地了知,或以特出的方式明顯地了知。清楚地領會者的情況就是正知(sampajañña),那即是以剛剛敘述的方式生起的智慧。
新疏:阿難陀長老(Ānanda Thera阿毗達摩疏鈔的作者)說:「清楚地領會就是廣泛地、正確地、平衡地了知(samantato, ammā, samaṁ vā pajānanaṁ sampajānaṁ),那本身就是正知。」
「以正知而行」的人就是習慣性地以正知做一切事務的人,或習慣性地練習正知的人。與註釋不同的另一種解釋法是:由於它引發(一切行動如)向前行等時的不痴,所以它是正知的練習。在內心練習正知的人就是「以正知而行」的人。
註:有四種正知,即:有益正知、適宜正知、行處正知及不痴正知。
疏:有益的是符合利益的,即:在佛法中成長的。有益正知就是清楚地了解在向前行等(一類活動)當中有什麼利益。適宜正知就是清楚地了解什麼對自己是適合的、有益的。行處正知就是清楚地了解自己托缽的去處,也是清楚地了解自己禪修法門之處,在從事向前行等其他活動時也不捨棄禪修。不痴正知就是對於向前行等(一類活動)不迷惑的正知。
註:(i)其中,有益正知是檢查(向前行的)行動以確定它是否值得做之後,了知有真實利益的洞察力。因此,當向前行的念頭生起時,修行者並不順從心的衝動而立刻向前行,而是先考慮:「向前行是否有真實的利益?」這裡所說的利益是指在佛法中成長,這可以藉著參訪佛塔、菩提樹、僧團、上座比丘、不淨對象(即可修行不淨觀的屍體)等來達成。因為藉著參訪佛塔或菩提樹,可以取佛陀為對象而引發喜悅,藉著參訪僧團可以取僧團為對象而引發喜悅,探究喜悅的壞滅與消逝可令人證悟阿羅漢果。藉著參訪上座比丘,修行者可以依循他們的教導來行持。藉著見到不淨的對象,可以引發初禪,探究初禪的壞滅與消逝可令人證悟阿羅漢果。因此,去參訪這些是有利益的。
疏:「證悟阿羅漢果」:這個解釋是講到最高的目標;然而,即使只是引發寧靜與觀智,那也是比丘的成長。
註:有些人〔無畏寺Abhayagiri Vihāra住眾〕說:得到物質日用品也是一種利益,因為那可以有助於修梵行;修梵行需依靠日用品的資助。
(ii)適宜正知是檢查向前行是否適宜之後,了知其適宜性的洞察力。例如參訪佛塔是有益的。但是,當舉行對佛塔的大供養法會時,多到可以覆蓋十或十二由旬地的大批群眾聚集在一起,男人與女人穿戴著適合他們身分的裝飾品四處遊逛,看起來就像色彩鮮艷的玩偶一樣。在這樣的場所,比丘可能會對可愛的對象生起貪欲,對可厭的對象生起瞋怒,對中立者生起愚痴。比丘也可能違犯身體接觸方面的戒條,或遭遇生命或梵行的障礙。如此,那地方就不適合去。然而,如果沒有這些障礙,那地方則是適合去的。去參訪菩提樹也可運用同樣的解釋。
去參訪僧團是有益的;但是,當人們在村裡建起一座大堂,安排通宵達旦的說法盛會,群眾聚集,而上述的障礙可能會發生時,如此,那地方就不適合去。如果沒有這些障礙,則那地方是適合去的。參訪被大批隨從圍繞的上座比丘也可運用同樣的解釋。
去看不淨的對象(即屍體)是有益的。下列的故事正可說明這一點:有一位年輕比丘帶著一個沙彌出外尋找作牙籤用的木料。沙彌走到大路之外,走一段路之後,他看見一具屍體。(以那具屍體作為禪修的對象,)他達到初禪。以初禪作為觀禪的基礎,他證悟前三個聖果(達到不還果)。他站在那裡觀察禪修的法門,以便進一步證悟下一個聖道(阿羅漢道)。這時候,年輕比丘由於見不到沙彌,就出聲叫他。沙彌心裡想:「自從出家以來,我不曾讓比丘需要叫我第二次。改天我再來修證下一個聖位吧。」於是他回答說:「什麼事,尊者。」比丘說:「過來。」沙彌立刻走過來,並且對比丘說:「尊者,沿著這條小路走一會兒,然後站在我剛才站的地方,面向東方,注視你的前面一會兒。」比丘照著做,結果也證得了同樣的聖位。如此,一具屍體令兩個人得到利益。
雖然(前去觀看)屍體是有益的,但女性屍體不適合男人;男性屍體不適合女人。只有與修行者同性的屍體才適合。
因此,適宜正知就是洞察事物是否合宜。
(iii)行處正知。行處(gocara)就是適合自己修行的業處(禪修法門)選自三十八種業處。比丘審察了有益與適宜,並且學習了自己的禪修業處之後,走在托缽的路上時一直將禪修業處保持在心中,這就是行處正知。要解釋這一點,必須了解下列這四種情況:(1)有的比丘將它帶去,但是沒有將它帶回;(2)有的比丘沒有將它帶去,但是將它帶回;(3)有的比丘沒有將它帶去,也沒有將它帶回;(4)有的比丘既將它帶去,也將它帶回。
疏:「將它帶去」:修行禪修業處,一心專注於業處,一直到托完缽要回來的時候。「但是沒有將它帶回來」:從他進食到返回到日間住處這段時間,他沒有將業處帶回來。
註:(1)「將它帶去,但是沒有將它帶回來」:在這四種比丘當中,第一種比丘在日間及初夜時都藉著行禪與坐禪來淨化自己的心,免除障礙(諸蓋)。他在中夜的時候睡覺。在後夜的時候再度坐禪與行禪。清晨的時候,他打掃佛塔與菩提樹的平台,給菩提樹澆水,注滿飲用與清洗水,如《犍度品》中所說的那樣執行對戒師與教授師等的各項義務。接著他照料自己身體的需要〔洗臉等〕,然後進入自己的住處,靜坐二或三次以重溫(自己的修行),專注於禪修業處。到了托缽的時候,他以專注於禪修業處的心,從座位上起來,拿起袈裟與缽,來到佛塔平台,都還是一直專注於禪修的業處。如果他的業處是佛隨念,那麼在進入佛塔平台時,他不需要放下自己的業處;然而,如果他所修的是佛隨念以外的其他業處,那麼,當他來到(通向平台的)台階底下時,他應當像放下手裡握著的一梱東西那樣地將業處放下。然後愉悅地以佛陀作為禪修的對象。走上平台之後,他應當繞塔三周。如果那是一座大塔,就在四個地方頂禮;如果那是一座小塔,就在八個地方頂禮。
頂禮佛塔之後,比丘應當來到菩提樹的平台,以謙恭的態度禮敬菩提樹,就像正面對著世尊佛陀一樣。如此禮敬佛塔及菩提樹之後,他回到之前放下禪修業處的地方(即台階下),就像用手拿起一梱東西那樣地拿起原先的業處。他的心中一直專注於業處。走到村外時,他覆蓋雙肩地穿著袈裟,然後入村去托缽。
村民們看見他時,叫說:「我們的尊者來了!」他們前來迎接他,接過他的缽,請他坐在他們的家裡或客廳裡,並且供養他稀粥。在食物正在被烹煮的時候,他們為他洗腳,在他的腳上塗油,然後坐在他的面前請教問題,或者表達想要聽法的意願。註釋師們說,即使他們沒有請求比丘說法,但是為了利益他們,比丘仍然應當為他們開示佛法,因為一切的佛法開示都是與禪修有關的。於是,比丘為他們開示佛法,用餐,然後表達謝意;做這一切事情的時候,他都一直將禪修的業處保持在心中。然後在村民們的陪同下,他告辭離去。儘管他不要他們相送,他們仍然送他走到村門口。走出村門口之後,他要村民們回去,而他自己則走上回寺院的道路。
那些在村外用過午餐的沙彌與下座比丘們見到這位比丘到來,都上前來迎接他,幫他拿缽及袈裟。據說古時候的比丘執行這項對上座們的義務時,不去看上座比丘是否他們的戒師或教授師。上座比丘一來到時,他們立刻執行他們的義務。
那些沙彌與下座比丘問他說:「尊者,那些村民是您的什麼人?是您父親那一方或母親那一方的親威嗎?」
他反問說:「為什麼你們會如此問?」
「因為看到他們對您如此的親切與崇敬。」
「諸位賢友,即使是我們的父母親都很難像這些村民這樣幫助我們。我們的缽與袈裟正是他們供養的。由於他們的護持,使我們在恐慌的時代安然不驚,在飢饉的時候飲食不缺。再沒有人比得上他們這樣利益我們了。」如此,他繼續講述他們的美德。這位比丘稱為「將它帶去但是沒有將它帶回的比丘」。
(2)「有的比丘沒有將它帶去,但是將它帶回」:另一位比丘清晨很早就執行上述的那些義務。當他那樣做時,業生的火大熾盛起來,而燒烤他的胃。他全身發汗,無法專注於禪修的業處〔因為身體受到飢餓逼惱的人無法妥善地專注〕。當天色還相當早的時候,他就拿起了缽與袈裟,匆忙地禮敬了佛塔,在村裡的牛群還沒有離開牛欄去吃草的時候,他就入村去托缽了。得到一些稀粥之後,他到客廳裡喝稀粥。當他才喝了二、三口的時候,他的業生火大就放掉他的胃,而改去抓取喝進來的食物。這時火大的燒烤熄滅了,他就像用一百桶清水沖浴過身體的人一樣。他以專注於禪修業處的心喝完剩餘的粥,洗缽,淨口。在兩餐之間的時間他都用來專注於自己的禪修業處。之後,他走到其他地方托缽,然後用餐,都一直保持心專注於禪修的業處。午餐後他返回寺院時,一直毫不間斷地專注於禪修的業處。這就是「沒有將它帶去但是將它帶回的比丘」。在佛陀的教化期中,如此喝粥後修行觀禪而證悟阿羅漢果的比丘有數不盡之多。單是在錫蘭島上,各個村落的客廳中,沒有一個座位不是比丘喝粥後證悟阿羅漢果的地方。
(3)「有的比丘沒有將它帶去,也沒有將它帶回」:第三種比丘過著放逸的生活。他疏怠於自己的職責,違反一切的義務。他的心受到五種牽絆與五種繫縛的障礙。他入村托缽時根本不曾想過有禪修業處這一回事。托缽及用餐時,他以不適當的方式與在家人交往。他內心空洞地回來。這稱為:「沒有將它帶去也沒有將它帶回的比丘」。
新疏:「他疏怠於職責」:他沒有激發精進心,沒有履行致力於禪修的職責。他藉著不實行義務而「違反一切的義務」。五種心的牽絆(cetokhīlā)與五種心的束縛(cetaso vinibandhā)在《中部.心牽絆經》(Cetokhīla Sutta, M.16)中有所解釋:
「諸比丘,什麼是未被捨棄的五種心的牽絆呢?在此,比丘懷疑導師,懷疑法,懷疑僧,懷疑戒,對梵行的同伴生氣。
什麼是未被斬斷的五種心的繫縛呢?在此,比丘還未去除對感官享樂的貪欲,還未去除對身體的貪欲,還未去除對色法的貪欲,吃飽之後就沉迷於睡眠之樂、懈怠、昏睡,由於渴望生天而修梵行。」(M.i.101-102)前一組(五種牽絆)由疑與瞋恨所構成,後一組(五種繫縛)由貪欲所構成。他「內心空洞地回來」因為他心裡沒有禪修業處。
註:(4)「有的比丘既將它帶去,也將它帶回」:這種比丘履行前去與返回的義務(gatapaccāgatavatta)。對於良家之子,謀求自身的福祉,而在佛教中出家。當他們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乃至一百人住在一起時,他們訂立如此的共同約定:「諸位賢友,你們來出家不是基於債務的逼迫、或基於恐怖的逼迫、或為求得生活的物質所需;你們出家乃是為了從痛苦中解脫。因此,如果在行走時內心生起煩惱,就在行走的當下將煩惱降伏。同樣地,如果在站立時內心生起煩惱,就在站立的當下將煩惱降伏;如果在坐著時生起煩惱,就在坐著的當下將它降伏;如果在躺臥時生起煩惱,就在躺臥的當下將它降伏。」
(沿著托缽的路上,)每隔半務薩帕、一務薩帕、半卡務塔、一卡務塔都放置著石頭。訂立如此的共同約定之後,每當這些比丘出外托缽的時候,他們內心專注於自己禪修業處地走著,藉著注意那些石頭〔來知道走到的地方〕。在行走當中,如果有比丘內心生起煩惱,他會在行走的當下就將煩惱降伏。萬一無法降伏,他就會停下來站著。跟隨在他後面的比丘也會跟著停下來站著。〔前面的比丘之所以停下來站著,是因為他不願意以沒有專注於禪修業處的心舉起腳來行走;後面的比丘之所以停下來站著,是因為他不願意超越前面的比丘。〕前面的比丘會訓誡自己說:「後面這位比丘知道你的心中已經生起染污的念頭;這樣的念頭對你而言是不恰當的。」如此訓誡自己之後,他修行觀禪,並且當下就證入聖者的境界。然而,萬一仍然無法降伏煩惱,他會坐下來。在他身後的比丘也會跟著坐下來等等,如前面所述。即使這位比丘無法證入聖者的境界,在降伏煩惱之後,他會專注於禪修業處地繼續行進。但是他不會以不專注於禪修業處的心舉起腳來行走;萬一他那麼做了,他會轉身走回來〔到他以不專注於禪修業處的心跨出第一步的地方,重新再走〕。
這種修行法的一個典範是走廊住者大摩天長老(Mahāphussadeva Thera)。據說他以十九年的時間來履行前去與返回的義務。工作中的人們──耕田、播種、打穀、做其他工作者──看見他以那種方式在路上行走,就互相談論說:「這位長老一再地轉回頭再走,是不是迷路了?或者他忘了什麼東西?」然而,長老一點也不在意別人的評議,只是一心專注於禪修業處,履行沙門的義務。在他第二十年雨季安居期間,他證悟了阿羅漢果。在他證悟的當天,住在他經行道的終端的一個天神站在那裡,由手指放射出光明。四大天王、帝釋天王及娑婆世界主梵天都來侍候長老。森林住者大提舍(Mahātissa Thera)長老見到了光明。隔天他來問大摩天長老說:「昨晚尊者這裡有光明,那是什麼?」大摩天長老移轉話題地說:「光明?燈火、珠寶都會有光明。」等等。但是大提舍長老緊追不捨地逼問說:「你在隱瞞自己的秘密。」最後,大摩天長老才承認,而講出自己的證悟。
另一個典範是住在黑蔓亭的大龍長老(Mahānāga Thera)。據說在履行前去與返回的義務時,第一次他發願要在七年的時間裡只採取站立與行走這兩種姿勢。心裡想:「我要禮敬世尊的大精進。」他再次履行前去與返回的義務十六年之後證悟了阿羅漢果。
疏:「只採取站立與行走這兩種姿勢」:這是指立定決心採取的姿勢,而不是指在用餐等必須坐著的時候也不坐下。「只」這一字是指不在(不需要躺或坐的)其他時候躺下或坐下。「世尊的大精進」是指世尊的苦行。這位長老心裡想:「為了我們的緣故,世尊修行了六年的苦行。我將盡我的全力來禮敬他。」以修行來禮敬世尊是最值得稱讚的禮敬方式;以物質供養來禮敬世尊遠不如以修行來禮敬。
註:他以專注於禪修業處的心舉起腳來向前走。如果以不注意於業處的心舉起腳行走,他會轉身走回來重走。走到村子附近時,他會停在人們(從村子裡看出來)還分辨不出他是牛或比丘的地方,穿著袈裟。以水瓶的水洗缽之後,他口中含著水。為什麼呢?他想:「當人們前來布施食物或禮敬我的時候,願我不會轉移對禪修業處的注意力,即使只是由於對他們說:『願你們長壽。』」但是如果人們問起當天的日期、寺裡比丘的人數或其他問題時,他會吞下那口水,然後回答。如果沒有人問起關於日期等問題,在離開村子時他會將水吐在村門附近,然後走上回程。
另一個典範是在迦蘭巴提達寺度過雨季安居的五十位比丘。他們在陽曆七月的月圓日立下這樣的協定:「只要還未證悟阿羅漢果,我們就不互相交談。」入村托缽時他們口中都含著水。當有人問起關於日期等問題時,他們會像上述那樣做。人們看著他們(離開村子時)吐在地上的水跡就能知道:「今天來了一位、兩位」等。村民們心裡想:「這些比丘只是單單不與我們講話,或是他們也不互相交談?如果他們不互相交談,那一定是他們之間發生了爭執。我們去勸他們和解吧。」來到寺院之後,他們見不到任何兩個比丘聚在一起。那群村民中的一位善於觀察的人說:「爭吵的人住的地方不會像這個樣子:佛塔與菩提樹的平台都打掃得很乾淨,掃帚排列得很整齊,飲水與用水準備得很妥當。」於是他們就回去了。那些比丘都在(雨季安居的)三個月內證得了阿羅漢果,並且在自恣日舉行了一次清淨的自恣。
如此,「將它帶去與帶回」的比丘就像住黑蔓亭的大龍長老與在迦蘭巴提達寺度過雨季安居的比丘們,他全心投入於禪修業處地提起腳向前行,走到村子附近時在口中含水。他先檢視街道,然後只走沒有醉漢鬧事與沒有狂象、狂馬的街道。托缽時他不會匆促地快速行走,因為托缽這項頭陀支不應快速地從事。相反地,他緩慢且安詳地走,就像行駛在崎嶇路上的水車那樣。
走到住家門口時,他會等候一段適當的時間,觀察那家的人是否想要布施食物。得到食物之後,他來到村內或村外的某個地方,或回到自己的寺院。在那裡,他專注於禪修業處地坐在一個舒適恰當的地點,先作食物可厭的觀想:他思惟取用食物就像為輪軸上油,為傷口塗藥膏,及像吃自己親生兒子的肉一般。然後在進食之時,他了知取用食物的八項因素,即:「我取用食物不是為了娛樂,不是為了沈迷,不是為了裝飾,不是為了美觀,只是為了支持身體、避免傷害與幫助梵行。」餐後,他漱洗,然後休息片刻,以去除用餐所造成的疲累。然後,在下午、初夜與後夜他就像在上午那樣地專注於禪修的業處。
藉著履行前去與返回的義務,在前去托缽時心中將業處「帶去」,返回時將業處「帶回」,有充分資助因緣的人能在人生的早期就證得阿羅漢果。若未在早期證果,則將在人生的中期證果。若未在中期證果,則將在臨死時證果。若未在臨死時證果,則將在(來世)成為天神時證果。若未在作天神時證悟阿羅漢果,那麼在還沒有佛出現於世間的時候,他會證悟成為辟支佛。若未能成就辟支佛,那麼就在又有佛陀出現於世間的時候,他會證悟阿羅漢果,就像婆醯尊者那樣的快速證悟者,或像舍利弗尊者那樣的大智慧者,或像大目犍連尊者那樣的大神通者,或像大迦葉尊者那樣的頭陀行者,或像阿那律尊者那樣具足天眼智者,或像優波離尊者那樣精通戒律者,或像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尊者那樣善於說法者,或像離婆多尊者那樣的森林住者,或像阿難陀尊者那樣的博學者,或像羅候羅尊者那樣的好學者。所以,在上述的這四類比丘當中,(托缽時將禪修業處)帶去與帶回的比丘達到了行處正知的顛峰。
(iv)不痴正知乃是在向前進等時候不迷糊。應當如下述來了解不痴正知。
在此,比丘在向前進或返回的時候對這些行動不迷惑,不像蒙昧的世間人那麼想:「自我在向前進,向前進的行為是由自我產生的。」或「我在向前進,向前進的行為是由我產生的。」相反地,他理智地了知:「當『我要向前進』這樣的念頭生起時,由那個念頭產生的心生風界會造成〔身體的〕動作。因此,藉著心理活動(所產生)風界的擴散,被認為是身體的這一組骨骼才會向前走。」向前走的時候,在每一次舉起腳的動作中地界與水界是次要與軟弱的,而另兩界〔風界與火界〕則是顯著與強力的。在腳向前移與腳跨出時也是同樣的情況。但是在腳向下落的時候,火界與風界是次要與軟弱的,而另兩界〔地界與水界〕則是顯著與強力的。在腳放在地面與腳向地面壓下時也是同樣的情況。
疏:藉著「自我在向前進」這句話,他顯示蒙昧的凡夫如何由於邪見的妄想而對向前進的動作生起迷惑。藉著「我在向前進」這句話,他顯示由於驕慢的妄想而生起迷惑。由於沒有貪愛的話,(邪見與驕慢)這兩項就不會生起,所以這也(隱喻地)顯示了由於貪愛的妄想而產生的無明。「相反地,他理智地了知」顯示如此透過破除密集(ghanavinibbhoga)而不迷惑。
「在每一次舉起腳的動作中」等:在舉起腳的動作中,火界是主要的動力因素,而風界則是輔助的因素。由於獲得風界之助的火界是舉起腳的條件,基於它們的能力,這兩界在此屬於主要。(由於缺乏該能力)其他兩界屬於次要。
「伸出腳與移動腳時也是如此」:在與地平線平行的動作裡,風界是主要的動力因素,因此它的作用在伸出腳與移動腳時很明顯,火界則是輔助的因素。由於獲得火界之助的風界是伸出腳與移動腳的條件,基於它們的能力,這兩界在此屬於主要。(由於缺乏該能力)其他兩界屬於次要。
雖然(在這兩種情況裡)火界與風界被分別為「協助者」(anugamaka)與「被助者」(anugantabba),基於它們的存在,註釋者把它們歸納在一起,而說「也是如此」。
「舉起腳」:把腳舉離踏足之地。
「伸出腳」:把腳伸越之前所立之地及伸向前。
「移動腳」:把腳向旁移以避開樹椿等或避免碰到另一隻踏在地上的腳。
或者,此二詞之間的差別可作如此理解:「伸出腳」是指把腳伸到另一隻踏在地上的腳之處;「移動腳」是指把腳移越那一點。
「將腳落下」:水界的本質比較沉重,而在將腳落下時,地界是它的輔助因素。由於獲得地界之助的水界是將腳落下的條件,基於它們的能力,這兩界在此屬於主要。(由於缺乏該能力)其他兩界屬於次要。
「置腳於地及保持腳踏在地面上時也是如此」:這麼說是因為獲得水界之助的地界是置腳於地的條件。保持腳踏在地面上就好像把腳固定住,此時,由於地界的作用特別強盛,水界是地界的輔助因素。同樣地,將腳向地面壓下的動作也是通過地界接觸的運作而完成;在此水界也是地界的輔助因素。
註:於此,舉起腳時發生的色法與名法不會維持到伸腳的階段。同樣地,在伸出腳時發生的那些(行法
= 色法與名法)並不能維持到移動腳的階段;在移動腳時發生的那些(色法與名法)並不能維持到將腳落下的階段;在將腳落下時發生的那些(色法與名法)並不能維持到置腳於地的階段;在置腳於地時發生的那些(色法與名法)並不能維持到保持腳踏在地面上的階段。
一段段、一節節次第地產生之後,這些行法都在那一處即壞滅,就有如在熱鍋裡爆裂的芝麻一般。其中,誰在向前走?向前走是誰的?在究竟界裡只有諸界在走著、諸界在站著、諸界在坐著及諸界在躺著。因為在每一段裡,連同色法:
一個心識生起,
另一心識壞滅,
名色次第生滅,
猶如水流不斷。
如是,「無痴正知」是在向前走等各方面沒有愚痴。這結束了對「向前行與返回時,比丘都以正知而行」這一句的含義的解釋。
疏:「其中」是指在向前行的動作裡,或在上述的舉起腳等每一個階段裡。「舉起腳時」是指在舉起腳的當下。「色法與名法」是指在舉起腳時產生的色法,以及產生該動作的名法。「不會維持到伸腳的階段」:因為它們只能維持一小段剎那。
「一段段、一節節次第地產生之後」等:應當明白,所提及的這一切是指舉起腳等每一階段(的名色法),基於它們屬於同一個相續流。
「這些行法都在那一處即壞滅」:無論它們在那裡生起,(它們)就在該處(壞滅)。因為行法不會從一處移到另一處(因為它們變化非常迅速)。連色法發生的時間也非常短暫,甚至比那些頭腳穿戴著利刃、喜歡旅行的年輕天神們向上向下地從相反方向相遇的時刻還要短暫。
「猶如在熱鍋裡爆裂的芝麻一般」:提及這點是為了顯示芝麻爆裂時發出爆裂的聲響象徵了芝麻爆裂,而行法之生起也是如此。
新疏:當然,諸行法不會真的在生起時發出爆裂的聲響;這麼說只是打個譬喻而已。猶如爆裂的聲響是芝麻爆裂的象徵,生起是諸行法壞滅的象徵,因為它們一生起就壞滅。
「誰在向前走?」沒有人在向前走。是否可以說:「向前走是誰的?」不可以。為什麼呢?「因為在究竟界裡只有諸界在走著」等等:這句話推翻了盲目愚痴的凡夫(所接受的)自我在向前走。或者,那些問題是以批評的方式提出來,而給予該答案「因為在究竟界……」則是用來去除該批評。
「在每一段裡」:在上述行走的六個階段的每一個階段裡。「連同色法」這一片語應當與該偈子中、以「生起」及「壞滅」(為結尾)的(兩)行連接起來。關於第一行,色法是任何(與心識)同時生起的色法。關於第二行,色法是指相同的色法;這些色法的壽命長達十七個心識剎那,在與它們同時生起的心識壞滅之後生起的第十七個心識的生時,它們已經生起(且存在),如今與這(第十七個)心識同時壞滅。否則可能有人會認為名法與色法的壽命相同。然而若果真是這樣,它就與註釋(《迷惑冰消》)所說的「色法變化慢,壞滅遲」互相違背,而且也違背經上的這段話:「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事物像心那樣快速變化。」(《增支部》1:49/i.10)緣取目標是心識與心所的本質,它們生起之後根據自己的能力顯現作為所緣緣的目標。因此,在實現(認識目標的)本質之後,它們就立刻壞滅。然而,色法不能緣取目標,而是被認識的目標。所以認識它們存在的過程經歷十六個心識剎那。因此色法的壽命等於十七個心識剎那,(那就是剛剛提到的十六個心識剎那)加上一個過去有分的剎那(在這剎那裡,色法已經生起,但認識它的過程還沒有發生)。
心識如此迅速地變化,因為它的發生只依靠迅速變化的心識與(受、想、行)三名蘊這些緣法接觸而已,也只依靠心識與它的目標接觸而已。色法的緩慢變化乃是由於(地、水、火、風)四界的遲鈍性所造成。然而,唯有如來才具有如實了知各界的智慧。藉著那樣的智慧,佛陀陳述只有色法是前生緣,藉著同樣的(智慧),佛陀也陳述後生緣。基於這點,認為名法與色法壽命相同是不妥當的。因此應當依照所解釋的來理解其含義。如此解釋這一點是因為比較容易明白(心)及與該心俱生的動作同時壞滅。
應當如此理解該(偈的)意義:另一個心與在它之前第十七個心識剎那時生起、與動作同時存在的色法同時壞滅。事實上,該偈的首兩行應當如此理解:
一個心識壞滅,
另一心識生起。
因為意義的順序與文字的順序不同。先前生起的心識壞滅之後,它成為在它之後即刻生起的心識的無間緣等等。因此「另一心識生起」擁有(先前生起的心識)為它的緣。這差別是根據它們的不同階段。
若是如此,可能會有批評指說在兩個(心識)之間有間隔。為了排除這種批評,他說:「水流不斷。」如是,名流與色流「猶如水流」般地發生,也就是猶如河水之流。
II. 向前看與向旁看時的正知
向前看或向旁看的時候,他以正知而行
註:在此,「向前看」是指看向前面的方向;「向旁看」是指看向旁邊。在這裡沒有提到其他種看的方式,如向下看、向上看與向後看。這裡只提到兩種方式,因為它們是適合的。或者藉著提到這兩種,其他種看的方式也都已包括在內。
其中,有益正知是先明瞭(向前看的)利益然後才行動,而不是受到「我要向前看」的念頭驅使就立刻向前看。這可透過難陀尊者的例子來理解。因為世尊說:「諸比丘,如果難陀想要看向東方,他會如此透徹地思惟:『在我看向東方時,願沒有貪、憂等邪惡不善心侵襲我。』之後,他才看向東方。他如此對該動作保持正知。如果難陀想要看向西方……北方……南方……上方……下方……四維之一,他會如此透徹地思惟:『在我看向四維之一時,願沒有貪、憂等邪惡不善心侵襲我。』之後,他才看向四維之一。(《增支部》8:9/iv.167)
疏:修行觀禪時,難陀尊者思惟:「由於沒有守護根門,我遭遇對佛陀教法生起厭煩等的不幸。我要善加收攝自己。」於是,他變得很熱忱,生起很強烈的慚愧心,結果在守護根門方面達到最高的成就。因此佛陀將他列為守護根門第一的大弟子。佛陀說:「諸比丘,難陀是我的眾比丘弟子中守護根門第一的弟子。」(《增支部》i.25)
註:再者,應當以前面在禮敬佛塔等章節中所解釋的方式來理解有益正知及適宜正知。行處正知就只是不捨棄禪修業處。是故在此取諸蘊、諸界與諸根門為禪修業處來修行的人,必須根據自己的禪修業處向前看與向旁看。對於修行遍禪等禪修業處的人,在向前看與向旁看時都應當一心專注地修行該禪修業處。
疏:其要意是不應該注意諸蘊等禪修業處以外的目標。
註:在此(關於在向前看與向旁看)的不痴正知是如此了知:「在內並沒有自我在向前看或向旁看。因此不痴正知就是如實地了知事物的真相。當『我要向前看』這樣的心生起時,它會產生心生的風界,而造成身體的動作。由於心生風界的擴散,下眼皮會向下開,上眼皮會向上開;沒有人用工具來將眼睛打開。接著眼識生起,完成了看的任務。」
新疏:提出上文是為了顯示由於向前看等的人只是某一組現象的過程,不痴正知是如實地了解該過程。「由於心生風界的擴散」:透過身體的動作,也就是包含(精神)活動的心產生的風界造成身體的動作。
註:再者,應當透過「根遍知」(mūlapariññā)、「外來客」(āgantukatā)及「短暫性」(tāvakālikabhāva)來了解不痴正知。
一、根遍知
有分與轉向,
眼識後領受,
推度與確定,
速行為第七。
其中,有分出現時,它完成了作為生命成分的作用。當它停止時,一個唯作意界生起,完成了轉向的作用;當這停止時,一個眼識生起,完成了看的作用;當這停止時,一個果報意界生起,完成了領受的作用;當這停止時,一個果報意識界生起,完成了推度的作用;當這停止時,一個唯作意識界生起,完成了確定的作用;當這停止時,速行次第生起七次。在這過程之中,向前看及向旁看時,受到「這是女人,這是男人」的念頭控制的貪瞋痴不會在第一或第二或甚至第七速行生起。然而,就像戰場上的士兵們一樣,當這些下面與上面的心次第地壞滅之後,就會有受到「這是女人,這是男人」的念頭控制的貪、瞋、痴在向前看或向旁看的時候生起。因此,首先應當透過根遍知來理解不痴正知。
新疏:「根遍知」是徹底地了解意門速行的根源。有分「完成了作為生命成分的作用」,因為它是(生命的)主要成分,這是因為它與結生心相似。或者它「完成了作為原因成分的作用」,因為它是(生命流)相續不斷的原因。
「在這過程之中……甚至第七速行」:這麼說是因為在前五門心路過程裡沒有受到「這是女人,這是男人」的念頭控制的貪、瞋、痴生起。當轉向與確定(這兩心)以不如理作意的方式生起時,速行純粹與貪同時緣取女人等可喜所緣生起,或純粹與瞋同時緣取不可喜所緣生起;但並沒有強烈的貪、瞋等生起。只在意門心路過程中才會有強烈的貪、瞋等生起。然而,前五門心路過程的速行心是接著生起的意門心路過程速行心中貪、瞋、痴生起的根源。或者所有在前面的有分心等(都可以作為根源)。如此,根遍知是透過意門速行的根源來說明。然而,「外來客」與「短暫性」則個別透過「之前不存在」與「一瞬即逝」於前五門速行來說明。
「然而,當這些下面與上面的心次第地壞滅之後」:這是指透過有分的次第生起。因為這些(心)的壞滅透過有分的生起而發生。論師以這點顯示,透過下面與上面的有分(那就是五門心路過程之前與之後的有分)的次第生起,與五門速行不同的意門速行生起。由於發生於該(意門速行的)貪等,論師說:「只有在那時候,才有受到『這是女人,這是男人』的念頭控制的貪瞋痴在向前看及向旁看時生起。」
二、外來客
註:當色塵呈現於眼門,在有分波動之後,轉向心(及隨後生起的諸心)次第生滅,完成了各自的作用,然後速行心生起。那速行心就像客人(āgantukapuriso)一樣,而眼門就像之前生起的轉向心等這些心的家一樣。就好像一個客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家庭乞討東西,在主人沉默不語的情況下,客人開口下命令是不恰當的。同樣地,在眼門這個家庭裡,當轉向心等本身沒有貪、瞋、痴時,作客的速行心有(強烈的)貪、瞋、痴是不恰當的。如是,應當透過外來客來了解不痴正知。
新疏:眼門被稱為「之前生起的轉向心等這些心的家」,因為它是它們發生的原因,因為它們只有在色塵呈現於眼門時才會發生。
「就像客人」:有兩種客人──受到邀請的客人與不速之客。受到邀請的客人是相熟的人,不速之客則是陌生人;在此的譬喻是指後者。
三、短暫性
註:在眼門裡生起的(轉向心直到)確定心與其相應心所(生起之後)就在當處壞滅。它們不會彼此相見,因此它們是一瞬即逝的、短暫的。就像在一戶家庭裡,其他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個垂死的人,在那時候,他不適合去享受唱歌與跳舞。同樣地,在一個根門裡,當轉向心等及其相應心所都死在它們生起的地方之後,剩下來不久將死的速行心不適合以貪、瞋、痴的方式去取樂。因此應當以短暫性來了解不痴正知。
此外,還應當藉著思惟蘊、處、界、緣來了解不痴正知。在此,眼根與色塵屬於色蘊;視覺屬於識蘊;與視覺相應的感受屬於受蘊;攝取印象屬於想蘊;觸等(心所)屬於行蘊。如是觀照向前看與向旁看只是這五蘊的結合。如此,那裡有誰在向前看與向旁看呢?
新疏:觀照向前看與向旁看只是五蘊的結合,那麼到底在這五蘊之外有誰在向前看呢?是誰在向旁看呢?其含義是:沒有人在向前看,也沒有人在向旁看。
註:再者,眼根是眼處;色塵是色處;視覺是意處;感受等相應心所是法處。如是觀照向前看與向旁看只是這四處的結合而已。如此,那裡有誰在向前看與向旁看呢?
再者,眼根是眼界;色塵是色界;視覺是眼識界;受等相應心所是法界。如是觀照向前看與向旁看只是這四種界的結合而已。如此,那裡有誰在向前看與向旁看呢?
再者,眼根是依止緣;色塵是所緣緣;轉向是無間緣、相續緣、親依止緣、無有緣、離去緣;光線是親依止緣;受等相應心所是俱生緣。如是觀照向前看與向旁看只是這些緣的結合而已。如此,那裡有誰在向前看與向旁看呢?
如是,在此也應當透過蘊、處、界、緣來了解不痴正知。
III. 屈伸肢體時的正知
屈伸肢體的時候,他以正知而行
註:這是指關節屈伸的動作。其中,有益正知是先思惟來確定屈伸手腳是否有利益(然後採取有利益的動作),而不是只隨著念頭生起就屈伸肢體。應當如此理解「先思惟來確定屈伸手腳是否有利益」。若人以彎曲或伸直的手或腳長久站立,就會持續地感到疼痛,而使心無法專注,他的禪修會退步,他則無法獲得卓越的成就。相反地,適時地屈或伸手腳的人不會感到疼痛,其心能夠專注,他也能成就自己的禪修業處,獲得卓越的成就。
適宜正知是即使對於有利益的事情也必須考慮適合或不適合做。這是該方法的解釋:
據說在大舍利塔的平台上,當年輕的比丘們在誦經的時候,年輕的比丘尼們就站在後面聽他們誦經。那時有一位年輕比丘在伸手時碰觸到一位比丘尼。就因為這樣,他還俗了。另一位比丘將腳伸進火堆裡,使到自己的腳被燒到見骨。又有另一位比丘將腳伸到蟻丘上,因而被毒蛇所咬。另一位比丘將手伸出放在衣帳的竿子上,而被一條花蛇咬傷。因此不應在不適宜的時候伸展肢體,而應當只在適宜的時候伸展。這是適宜正知。
關於行處正知則可藉一位大長老的故事來說明。據說,當這位大長老坐在日間住處對他的弟子們說話時,他快速地彎起手臂,接著將手臂放回原位,然後再一次慢慢地彎起手臂。他的弟子們問說:「尊者,為什麼您快速地彎起手臂,接著將手臂放回去,然後再度慢慢地彎起手臂呢?」長老回答說:「諸位賢友,自從開始修行禪修業處以來,到目前為止我還不曾以不專注於禪修業處的心彎起手臂。因此我將手臂放回原位,然後再度將它彎起來。」他的弟子們說:「善哉,尊者!比丘正應該如此做。」在這裡,應當了解不捨離禪修業處就是行處正知。
在此(關於屈伸肢體),應當如此理解不痴正知:「在內並沒有自我在彎曲或伸直肢體。只是由於心生風界的擴散,才產生屈和伸的動作,就好像拉扯木偶的線就能移動它的手腳。」
IV. 穿著袈裟等時的正知
穿著袈裟、執持衣缽的時候,他以正知而行
註:在此,「穿著袈裟」是指穿著上衣與下衣,「執持缽」則是指用缽來接受缽食等。其中,應以世尊所指出的各種目的來理解有益正知:「穿著袈裟及托缽時,他(思惟)物質利養只是為了『避免寒冷』等等。」
應當如此理解適宜正知:薄的袈裟適合熱性體質的人與身體虛弱的人。對於怕冷的人而言,由兩層布重疊而縫製的厚袈裟是適宜的。與這些情況相反的袈裟則不是適宜的。穿壞了的袈裟對每個人都不適宜,因為它需要修補與縫製,因而成為一種障礙。同樣地,絲綢、細緻等高級材料所製成的袈裟也不適宜,因為它們會激起貪心。因為如果比丘單獨住在森林裡,那樣的袈裟可能會造成他住宿的障礙或危害他的生命。嚴格來說,透過暗示等邪命方法獲得的任何袈裟,以及會使善法衰減、惡法增盛的袈裟,無論如何都不適宜。與這相反的則適宜。
行處正知就是不捨離禪修的業處。
在此,應當透過下列的思惟來理解不痴正知:「在內並沒有一個自我在穿著袈裟,只是藉著心生風界的擴散,而有穿著袈裟的動作產生。其中,袈裟與身體都沒有思考能力。袈裟不知道:『身體被我覆蓋著。』身體也不知道:『我正被袈裟覆蓋著。』僅僅是一堆法覆蓋另一堆法而已,就像一塊布蓋著人體模型一樣。因此不需要因為得到精緻的袈裟而歡喜,或因為得到粗劣的袈裟而沮喪。
有些人用花環、香水、香、布等供品去禮拜有眼鏡蛇居住的蟻丘、聖樹等對象。另外有些人則以糞便、尿液與爛泥、棍擊、刀砍來褻瀆它們。然而,蟻丘、聖樹等不會因此而歡喜或沮喪。同樣地,比丘不應因為得到好的袈裟而歡喜,或因為得到不好的袈裟而沮喪。」
新疏:以「身體沒有思考能力」,論師指出身體跟袈裟一樣沒有自我。如此解釋,他指出滿足於所獲得之物的理由。
註:持用缽時應當透過思惟持缽所得之物的目的來了解有益正知。不慌不忙地持缽及思惟:「以此托缽我將得到食物。」
應當如下地理解適宜正知。身體瘦弱的人不適合用重的缽。破損至有四、五個補處、難以妥善清洗的缽不適合任何人用。難以妥善清洗的缽不適合用,而且會障礙洗缽的人。正如上述有關袈裟理由,亮麗如珠寶一般的缽會激起貪心,因此是不適當的。透過暗示等邪命方法所得的缽,以及會使善法衰減、惡法增盛的缽無論如何都非常不適宜。與此相反的則適宜。
應當了解行處正知就是不捨棄禪修業處。
應當根據以下的思惟來理解不痴正知:「在內並沒有一個自我在拿取缽。正如前面講過的,只是藉著心生風界的擴散,所以才有拿取缽的動作產生。在這件事情上,缽不會想,手也不會想。缽不會知道:『我被手拿著。』手也不會知道:『缽被我拿著。』只是一堆法拿取另一堆法而已,正如用火鉗來夾取火紅的缽一樣。」
再者,當善心人士看見許多人躺在一間庇護所裡──手足殘缺;裸露的傷口中充滿膿、血和蛆;身體佈滿蒼蠅──善心人士送給他們繃帶及罐裝的藥等等。有些受難者得到柔軟的繃帶,有些則得到粗糙的繃帶;有些得到像樣的藥罐,有些則得到畸形的藥罐。然而,這些病人不會因此感到歡喜或沮喪,因為他們只是要用繃帶來包紮傷口、用藥罐來存放藥而已。同樣地,將袈裟視為繃帶、將缽視為藥罐、將缽裡的食物視為藥的比丘可說是透過穿著袈裟、執持衣缽之不痴正知來修行正知的上等修行者。
V. 吃與喝等時的正知
吃、喝、咀嚼、嚐味的時候,他以正知而行
註:在此,吃是吃軟食,喝是喝粥等,咀嚼是咀嚼糕點等硬食,嚐味則是品嚐蜂蜜、糖漿等。
在每一種情況裡都有八項目的,記載於有關取用食物的用處的標準思惟法。應當如此了解有益正知。
應當如下地理解適宜正知。無論食物是粗糙或精緻、苦或甜等等,只要會造成身體不舒服的食物就不適宜。透過暗示等邪命方法所得來的食物,以及食用之後會使善法衰減、惡法增盛的食物無論如何都是非常不適宜。與此相反的則適宜。
行處正知就是不捨離禪修業處。
應當根據以下的思惟來理解不痴正知:「在內並沒有自我在吃。正如前面所說的,只是藉著心生風界的擴散,才有以缽接受食物的動作生起。也只是藉著心生風界的擴散,才有伸手進入缽中、食物被捏成一團、食團被拿出缽外及嘴巴張開,並沒有人用潤滑油或工具將嘴巴打開。只是藉著心生風界的擴散,食團才被放進口中、上排牙齒執行杵的作用、下排牙齒執行臼的作用、舌頭執行手的作用。如此,口中的食團在舌尖與稀薄的唾液混合、在舌根與濃稠的唾液混合,在下排牙齒臼裡,被舌頭翻攪、被唾液濕潤、被上排牙齒杵細細地研磨。此食物並沒有被任何人用杓子或湯匙放進(胃)裡面,只是藉著風界的作用而向前進行。進(胃)裡面時,沒有人用草蓆將吞進來的食物接住,只是由於風界的作用,食物才保持在原位。當它停留在(胃)裡面時,沒有人在裡面用火爐生火來煮食物,只是藉著火界的作用,食物才被消化。沒有人用棍子或棒子將消化後的食物推出(胃)外,將消化後的食物排出(胃)的是風界。
如是,風界把食物拿進(嘴裡),把它推下(胃裡),並且支持它、翻轉它、粉碎它、為它去除液體及把它排出去。地界也支持它、翻轉它、粉碎它及為它去除液體。水界濕潤它及保持其濕度。火界消化吞進來的食物。空界作為〔食物進入、翻轉、排出的〕通道。識界根據適當的精進來照顧這個或那個。」
新疏:「識界」是意識界,因為這是指識知尋食、取用食物等。「照顧這個或那個」:照顧尋食、取用食物等。「根據適當的精進」:完成每一項作用的精進,也是識知這些作用的緣。透過精進,人們完成尋食等,也完成識知取那(動作)為目標之法,因為精進對識知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照顧」:它透過體驗尋食、取用食物、已消化或未消化的狀態等轉向與識知尋食、取用食物、已消化或未消化的狀態等。或者,「適當的精進」是指正確的修行,「照顧」則是指思惟:「在內並沒有自我在吃」等等。
註:再者,應當透過下列十種方面思惟食物的可厭性來了解不痴正知:走、尋求、吃、分泌、儲藏所、未消化的狀態、已消化的狀態、結果、流洩出去及污染。關於這一點的詳細解釋,應當依照《清淨道論》(第11章.第1-26節)的「食厭想論」來理解。
新疏:「走」:走去托缽的村莊;回來也包括在這裡,因為它也是屬於走。「尋求」:在村莊裡托缽,這包括回來及走進托缽堂等,因為這些也屬於尋求。「吃」:吃食物時,食物被牙齒杵細細地研磨、被舌頭翻攪,這時候的食物變得非常可厭,就好像狗吐在狗盤裡的食物一樣可厭,變成一種怪怪的混合物,失去了它(原有)的顏色與香味。
「分泌」:膽汁、痰、膿與血這四種分泌在胃的上方;當吃下的食物遇到這些分泌時,它們使它變成非常可厭。
「儲藏所」:如此稱呼胃(為儲藏所)是因為當食物被吃下去後就停留與積累在這裡。「未消化的狀態」:吃下去的食物還沒有被負責消化的業生火完全消化的狀態。「已消化的狀態」:已經完全被上述的業生火完全消化的狀態。
「結果」:它的後果,也就是它的目的。當吃下去的食物受到正確的消化之後,它產生可厭的身體部分,例如頭髮等;當它沒有受到正確的消化時,它產生疾病,例如皮疹等。
「流洩出去」:透過眼、耳等諸門排泄廢物。正如所說:
極度享受之飲食,
硬的咀嚼軟的吞,
全部經由一門進,
卻從九門洩出去。
「污染」:吃的時候,雙手、嘴唇及其他的身體部分都沾滿了食物;吃完後,該九門則被染污了。
應當以這一切方式來思惟食物之可厭性。
VI. 大小便利時的正知
大小便利的時候,他以正知而行
註:在此,應該大小便的時候如果不大小便,那麼身體會出汗、眼睛會眩暈、心無法專注,以及會產生各種疾病。相反地,如果在應當大小便的時候大小便,這些就不會產生。這是有益的,應當如此了知大小便時的有益正知。
如果在不適當的地方大小便,則(比丘)觸犯戒律,得到不好的名聲,甚至可能危害自己的生命。如果在適當的地方大小便,這些就不會發生。這是適宜的,應當如此了知大小便時的適宜正知。
應當了解行處正知就是不捨離禪修業處。
應當根據以下的思惟來理解不痴正知:「在內並沒有一個自我大小便,只是藉著心生風界的擴散,而有大小便的行為產生。就像一個成熟的膿皰破裂時,不需要任何意願促使,膿血會自動地流出來。也像水壺裝水裝得太過滿時,不需要任何意願促使,水會自動地流出來。同樣地,積聚在大腸與膀胱裡的糞與尿被風界的力量壓出體外,不需要任何意願促使。當然,如此排出來的糞與尿不是那個比丘的,也不是別人的,只是身體的排泄物而已。怎麼說呢?當一個人倒掉水盆裡的髒水時,倒掉的髒水不是他的,也不是別人的,它只是舊的洗用水而已。
新疏:「它們不需要任何意願促使地排泄出來」(akāmatāya):這麼說是為了排除愚痴的見解──認為有個自我使得它們排泄出來,以及它們被排泄出來是透過該自我的意願。意思是它們只是藉著心生風界的擴散排泄出來,不需要任何自我的意願與努力。
VII. 次要姿勢的正知
走路、站立、坐著、入睡、醒來、說話或沉默的時候,他以正知而行
註:以下的經文解釋長時間的姿勢:「行走時比丘了知:『我正在行走。』站立時比丘了知:『我正在站著。』坐著時比丘了知:『我正在坐著。』躺臥時比丘了知:『我正在躺著。』」(《中部》10/i.56-57)
中等時間的姿勢在上述(第一組正知)的經文解釋:「向前行與返回時,向前看與向旁看時,彎曲與伸直肢體時,他以正知而行。」但在此,透過「走路、站立、坐著、入睡、醒來」這些話,則解釋了次要的姿勢。因此,應當以這裡的敘述來了解這些情況的正知。
然而,三藏法師摩訶尸婆長老(Elder
Tipiṭaka Mahāsiva)則如下地解釋:一個人在走了很遠或來回經行(修禪)很久之後,停下來站著,內心思惟著:「來回經行時存在的名色法已經在那裡壞滅了。」這就是走路時以正知而行的人。
一個人站著背誦、回答問題或修禪很久之後坐下來,內心思惟著:「站立時存在的名色法就在站立時壞滅了。」這就是站立時以正知而行的人。
一個人坐著背誦等等很久之後起身,內心思惟著:「坐著時存在的名色法就在坐著時壞滅了。」這就是坐著時以正知而行的人。
一個人躺著背誦或修禪時睡著了,醒來之後內心思惟著:「睡眠時存在的名色法就在睡眠時壞滅了。」這就是入睡與醒來時以正知而行的人。因為睡眠時沒有活躍的心識發生,覺醒時它們則發生。
一個人說話時正念地說話且清楚地了知:「聲音依靠嘴唇、牙齒、舌頭、上顎及心的適當精進而生起。」這就是說話時以正知而行的人。
或者,一個人以一段長久的時間從事背誦、講解佛法、講解禪修業處或回答問題,然後安靜下來,內心思惟著:「說話時存在的名色法就在說話時壞滅了。」這也是說話時以正知而行的人。
一個人沉默地思考佛法或修禪一段長久的時間之後,如此思惟:「沉默時存在的名色法就在沉默時壞滅,所造色(聲音)生起時人在說話,這種所造色不生起時是沉默。這就是沉默時以正知而行的人。
摩訶尸婆長老著重於不痴的解釋是根據《大念處經》(的教法)。然而,在這部《沙門果經》裡,所有四種正知都受到重視。所以應當依照以上解釋的四種正知來理解正知。
新疏:摩訶尸婆長老解釋的以正知而行是觀照之前的姿勢裡的名色法在該處即壞滅,因此應當依照記載於《大念處經》中的不痴正知,也就是修行觀禪來理解(他所解釋的以正知而行),而不是依照四種正知來理解。因此他的解釋是針對那裡(《大念處經》),而不是針對這裡(《沙門果經》)。由於此教法的主要目的是指出沙門行的殊勝成果,在此四種正知都受到重視。因此這是這裡(《沙門果經》)含義。
註:(經文中)說到「他以正知而行」時,應當理解在一切詞句裡都是指與正念相應的正知而已。因為這段經文是「他具備正念與正知」這一片語的詳細解釋。再者,《分別論》(Vibhaṅga)如此分析這些片語:「他保持正念與正知地前進;他保持正念與正知地返回……」
新疏:「與正念相應的正知」:論師以這點指出,就好像透過正知的作用來了解正知的重要性,對於正念也是如此。但這不只是指出正念與正知相伴而生的情況而已,因為智不會沒有正念地生起。」
為了解釋為何應當透過與正念相應的正知來理解其含義,論師說:「因為這段經文是『他具備正念與正知』這一片語的詳細解釋。」如是,由於該經文闡明提及(正念與正知)兩者的片語,因此可以接受該義釋跟總說一樣同等地注重正念與正知兩者。
為了再以《分別論》的教法來證明這一點,論師說:「再者,《分別論》……」《分別論》分析了「這些片語」──義釋的片語,例如「向前行時,他以正知而行」等等。這也就是說在一切情況裡,它們都受到個別的分析,沒有把正念歸納在正知之內。
然而,中部誦者與阿毗達摩論師們說:「行走時,有比丘思惟某個東西地行走,卻又想著另一個東西;另一位比丘則不棄離禪修業處地行走。同樣地,站立、坐著與躺臥時,有比丘思惟某個東西地躺臥,卻又想著另一個東西;另一位比丘則不棄離禪修業處地躺臥。但是(他們說)到這個程度行處正知還不明顯。他們以在經行道(修習行禪)的例子來闡明他們的看法。
有位比丘在走進經行道之後,站在經行道的一端,然後觀照:「存在經行道東端的名色法就在東端壞滅,不會到西端來。存在經行道西端的名色法就在西端壞滅,不會到東端來。存在經行道中央的名色法就在中央壞滅,不會到兩端來。來回行走時的名色法就在行走時壞滅,不會到站立時來。站立時的名色法就在站立時壞滅,不會到坐著時來。坐著時的名色法就在坐著時壞滅,不會到躺臥時來。躺臥時如此一再地觀照,他睡著了。醒來時他立刻專注於禪修業處。這樣的比丘就是行走等時以正知而行的人。
入睡時,業處會變得不清楚;但不應讓業處變得不清楚。因此,在經行時、站立時、坐著時(修禪)之後,比丘盡力在躺臥時如此觀照:「身體沒有知覺,床也沒有知覺。身體不會知道:『我躺在床上。』床也不會知道:『身體躺在我上面。』只是沒有知覺的身體躺在沒有知覺的床上。」如此一再地觀照,他的心就進入有分。醒來之後他立刻專注於業處。這就是有正知地入睡的人。
一位比丘如此觀照:「速行,或所有透過六門產生之法,是具有活動的特點的過程,因為它的特點是它產生的身表等等,也因為它由轉向的活動產生;當這存在時,甦醒就發生。」他(這種比丘)就是醒來時以正知而行的人。再者,把一晝夜分為六個階段,然後在其中五個階段保持醒覺的人也稱為醒來時以正知而行的人。
有人開示佛法,因為它是解脫的基礎,而且捨棄了三十六種廢話,只說十種適宜的課題,這種人是說話時以正知而行的人。
有人把專注力導向他自己喜歡的三十八種業處之一,而證得了第二禪,這種人是沉默時以正知而行的人。第二禪特別地被稱為沉默,因為它沒有思考活動。
大王,比丘如此具足正念與正知
註:它的意思是:「如此,透過與正念相應的正知來實行向前行等(動作),他具備了正念與正知。」
知足(santosa)
66. 大王,比丘如何知足呢?在此,大王,比丘滿足於保護身體的袈裟與果腹的缽食
註:他知足於任何資具。此知足有十二種。關於袈裟有三種知足:依自己所得而知足、依自己的力量而知足及依適宜的而知足。相同的三種分類也適用於缽食及其他(兩種)資具(住所與藥物)。接下來是詳細解釋。
(一)袈裟:在此,有比丘獲得一件袈裟,(無論)該袈裟的品質高等或下等,他就只穿著該袈裟,沒有欲求獲得其他袈裟。這就是他依自己所得的袈裟而知足。
另一位比丘體弱,或患了病,或已年老,因此穿著重的袈裟時感到疲累。於是他與一位親切的比丘交換袈裟,知足於穿著輕的袈裟。這就是他依自己的力量而對袈裟知足。
另一位比丘獲得上等品質的資具。獲得貴重的缽或袈裟,或獲得許多缽與袈裟時,他把它們拿去布施,心想:「這適合出家多年的長老們;這適合那些飽學者;這個應當給生病的比丘們;這個應當給那些只獲得少許(資具)者。」他自己則取用他們的舊袈裟,或去垃圾堆拾取破布來做袈裟,而且知足於穿著它。這就是他依適宜的而對袈裟知足。
(二)缽食:在此,有比丘獲得粗劣或殊勝的缽食。他即以該缽食維生,不欲求其他任何食物;即使獲得其他東西,他也不接受。這就是他依自己所得的缽食而知足。
另一位比丘獲得不適合他的身體或健康的缽食,以致如果吃了他就會生病。因此,他把該食物給與一位親切的比丘,在吃了後者給他的食物之後,他滿足於實行沙門的任務。這就是他依自己的力量而對缽食知足。
另一位比丘獲得極其殊勝的缽食。跟袈裟的情形一樣,他把該食物給與出家多年的長老、飽學者、少得者及病患,而他則知足於食用他們剩餘的食物;或者,托缽過後,他知足於食用(他缽中)摻雜在一起的各種食物。這就是他依適宜的而對缽食知足。
(三)住所:在此,有比丘獲得令人愉悅或不愉悅的住所。他不會因此而感到快樂或憂鬱,而滿足於所獲得的任何住所,即使那只是一張草蓆。這就是他依自己所得的住所而知足。
另一位比丘獲得不適合他的身體或健康的住所,以致如果住在那裡他就會生病。因此,他把該住所讓給一位親切的比丘,而知足地住在屬於後者的適宜住所。這就是他依自己的力量而對住所知足。
另一位比丘有大福報,獲得極其殊勝的住所:山洞、殿堂、尖頂屋等。跟袈裟的情形一樣,他把該住所讓給出家多年的長老、飽學者、少得者及病患,而他則知足於住在任何處所。這就是他依適宜的而對住所知足。
再者,有比丘可能會思惟:「殊勝的住所是放逸的根源。坐在裡面會昏沉與睡眠。昏沉入睡後醒來時,欲念就會生起。」如此思惟,他不接受任何這類的住所,即使是特別給他的。他拒絕它,而知足於住在空地或樹下等等。這也是他依適宜的而對住所知足。
(四)藥物:在此,有比丘獲得粗劣或殊勝的藥物。他知足於所獲得的(藥物),不欲求其他任何(藥物);即使獲得其他東西,他也不接受。這就是他依自己所得的藥物而知足。
另一位需要油的比丘獲得糖漿。因此,他把該它給與一位親切的比丘,在從後者或其他地方獲得油之後,他知足於取用它為藥。這就是他依自己的力量而對藥物知足。
另一位比丘有大福報,獲得許多極其殊勝的藥物:油、蜂蜜、糖漿等等。跟袈裟的情形一樣,他把它給與出家多年的長老、飽學者、少得者及病患,而他則知足於他們給他的任何藥物。如果他們把橄欖果與牛尿放在一個罐子裡,以及把四種糖放在另一個罐子裡,然後向他說道:「尊者,請隨意拿取您所要的。」假如這兩者都能夠治癒他的病,他就會想:「橄欖果與牛尿這種藥是諸佛所讚歎的。」因此他拒絕接受四種糖,而極其知足地取用橄欖果與牛尿作為藥。這就是他依適宜的而對藥物知足。
具備這十二種「知足於任何資具」的比丘可以取用八種資具:三衣、一缽、一把用來削牙籤的刀、一支針、一條腰帶及一個濾水器。
所有這些資具都有「保護身體」與「果腹」的目的。如何?四處遊方時,若人穿著三衣,他就是維持與保護身體;如是這些(袈裟)是為了保護身體。喝水時,若人先用袈裟的一角來過濾水,或用袈裟來接受要吃的水果,他就是維持與保護身體;如是這些(袈裟)是為了果腹。
若人用缽來取水洗澡或調合黏土來修理其僧舍是為了保護身體,若在用餐時用缽來接受食物則是為了果腹。
若人用刀來削牙籤或修平其床腳與床面、椅腳與椅面、或帳篷的柱子是為了保護身體,若用來切甘蔗或開椰子等等則是為了果腹。
若人用針來縫製袈裟是為了保護身體,若在用餐時用它來挑起水果或糕點則是為了果腹。
若人在出外之前戴上腰帶是為了保護身體,若用來綁甘蔗等則是為了果腹。
若人在洗澡或為自己的住所塗上黏土時用濾水器來過濾水是為了保護身體,若用它來過濾食水或在用餐時用它來接受芝麻、米或蜜果則是為了果腹。
這是取用八種資具者的資具界限。但是對於取用九種資具者,當他住在寢室裡時,裡面的床單或鎖匙是許可的。對於取用十種資具者,椅子或獸皮是許可的。對於取用十一種資具者,拐杖或油瓶是許可的。對於取用十二種資具者,陽傘或一雙涼鞋也是許可的。
但是不應該說在這些比丘之中只有取用八種資具者才知足,其他比丘則不知足、多欲、難護持。因為他們也知足、少欲、易護持、生活簡樸。然而,世尊並非依據那些比丘來這部經,而是依據取用八種資具者來解釋。因為此人用濾水器包住他的小刀與針,再把該濾水器放進他的缽裡,然後把缽掛在肩膀上,穿上三衣,戴上腰帶,愉快地去他想要去的地方。沒有東西需要他倒回頭來拿。如此顯示這種比丘的簡樸生活,世尊說:「比丘滿足於保護身體的袈裟與果腹的缽食……」
無論去到那裡,他都隨身只攜帶著(資具)
註:離開時他只把所有八種資具帶在身上。他不會執著「我的寺院、我的房間、我的侍者」。他就像從弓釋放出去的箭,或像因為生活刻板而捨離象群之象。他獨立獨坐地住在任何他喜歡的住所:森林、樹下、山腰的樹林。在一切姿勢裡,他都獨自一人,沒有伙伴。如此,他的行為就像是(《經集.犀牛經》v. 42)解釋的犀牛行為:
四方世界作為家,
心中不含瞋恨念,
一切所得皆知足,
面對諸難不沮喪──
應當獨行如犀牛。
就像鳥兒一樣,無論飛到那裡,都只以兩翼為牠的唯一負擔
註:佛陀接著以鳥的譬喻來顯示這一點。這是它的簡要含義:聽到某某地方有一棵樹長滿了成熟的果實,眾鳥從各方到來吃那些果實,用爪、翼、喙拾取與撕裂它們。牠們不曾想:「這是今天的食物;那是明天的食物。」果實被吃完之後,牠們既不在該樹四周保護它,也不在該處留下羽毛、爪印或喙印。反之,牠們不再留戀該樹,每一隻鳥都隨意飛向其他地方,飛走時都只以兩翼為唯一負擔。同樣地,該比丘隨意去他所要到之處,沒有執著,沒有留戀。所以說:「他隨身只攜帶(自己的資具)離去。」
棄除五蓋(nīvaraṇappahāna)
67. 具足了此聖潔的戒蘊、聖潔的諸根律儀、聖潔的正念與正知及聖潔的知足之後,他前往寂靜的住處
註:佛陀以此顯示了什麼?他顯示了獲得住在森林裡的先決條件。因為缺少這四種先決條件的人不能成功地住在森林裡,只能歸納為與動物或森林流浪人同類。住在該森林裡的眾神會想:「如此邪惡的比丘住在森林裡有什麼用?」他們將會製造可害的聲響,用手擊打他的頭,使得他逃走。他也惡名昭彰,有(如此)關於他的傳聞:「某某比丘進入森林之後做了這樣及那樣的壞事。」
然而,已經獲得這四種先決條件的人則能成就其森林生活。省察自己的戒行,他不見有任何污染或瑕疵,因而激起了喜悅。觀照喜悅的生滅,他證入聖者之界。住在該森林裡的眾神感到滿意,而且讚歎他。他美名遠播,猶如掉入水中的一滴油。
其中,「寂靜」是指空蕩,也就是安靜、無噪音。《分別論》即是針對這一點而說:「『寂靜』:即使是在近處的住所,如果沒有擠滿在家眾或比丘眾,那麼它就是寂靜。」一個住處(senāsana,直譯為「床及椅子」)是人躺臥與坐下之處;它是床及椅子的名稱。所以說:「『住處』:床是住處;椅子是住處;坐墊、枕頭、住所、斜頂屋、尖頂屋、平頂屋、天然山洞、多層華宅、圓屋、石洞、竹林、樹下及會堂也都是住處。或者,比丘會回去的任何地方就是住處。」(《分別論》)
再者,住處有四種,如下:住所、斜頂屋、尖頂屋、平頂屋及天然山洞稱為「住所住處」;床、椅子、坐墊及枕頭稱為「床椅住處」;小地毯、獸皮、草蓆及葉蓆稱為「蓆子住處」;「或者,比丘會回去的任何地方」稱為「生活空間住處」。這一切都包括在「住處」這一詞之內。
然而,佛陀在此指出的是適合像鳥一樣四海為家的比丘的住所。所以他說:「他前往寂靜的住處。」其中,「森林」對於比丘尼來說是作為村莊界標的柱子以外的地方,但對於在此所提到的比丘,他的森林住處必需最少離開村莊五百弓遠才適合。其特徵在《清淨道論》的「頭陀支論」中有解釋。
「樹下」是任何寂靜處的陰涼樹下。「山丘」是石頭山丘。在石池裡洗澡及喝水之後,若人坐在陰涼的樹下,涼風陣陣地輕拂在身上,四處可見,心就會變得專注。
「幽谷」是被水分隔的山區;有人說那是河水奔騰怒吼之處。因為該處的沙好像銀箔,頭上方的樹林好像鑲嵌著寶石的華蓋,水流則好像一堆的珠寶。進入這樣的幽谷、喝了水、清涼肢體、堆積一個沙堆、以糞掃衣準備好座位之後,若人坐下來實行沙門的任務,心就會變得專注。
「山洞」是兩座山之間的大隙縫,或是在單一座山裡、像隧道般的大隙縫。「墳場」的特徵在《清淨道論》中有解釋。「叢林」是村莊郊外之外、沒人到訪、沒人耕種的地方。所以說:「『叢林』:這是偏僻住處的名稱。」「空地」:沒有蓋的地方。想要住的人可以搭帳篷住在這裡。「草堆」:一堆的稻草。從一大堆的稻草拿取了一堆稻草之後,他們搭建了一個好像山洞一般的住所。他們也把稻草丟在草叢、矮樹叢等之上,然後坐在它的下面,實行沙門的任務。
他盤腿而坐,保持身體正直,建立正念在自己面前
註:「他盤腿」:他交叉雙腳,使得雙腿完全固定。「他保持身體正直」:他保持上半身正直,十八節脊椎骨節節平正地相接。對於這麼坐的人,皮膚、肌肉與腱不會向前彎,所以因為它們向前彎而生起的陣痛就不會產生。由於那些(痛苦的)感受沒有產生,心變得專注,禪修業處也不會退失,反之達到成長、成就與成熟。
「建立正念在自己面前」:他運用正念於自己的禪修業處;或者他安立正念於嘴巴那一帶。所以《分別論》說:「此念被建立、妥善地建立在鼻尖或口相。」
新疏:「口相」(mukhanimitta)是上唇的中部(人中),空氣出入鼻孔時磨擦之處。
68. 捨棄對世間的貪欲之後……
註:在此,五取蘊是世間(loka),因為它毀壞(lujjana)與分解(palujjana)。所以在此其意是:捨棄對五取蘊的貪欲、鎮伏貪欲之後。
「他以無貪的心來安住」:以透過鎮伏貪欲而無貪之心,並非好像眼識〔自然地無貪〕。
「他使心從貪欲中淨化出來」:他使心從貪欲中解脫出來;他捨棄貪欲且不再執取它地行事。
新疏:淨化(心)是指當下釋放它,而且未來不再拾起它地行事。就好像其心透過遍作修習淨化而無貪一般,同樣地,它也變得無瞋恨、無昏沉睡眠、無掉舉追悔、無懷疑。
註:「惡意」:心因它而患了病,猶如惡臭的粥捨棄了本質。「瞋恨」:人(因它)變得畸形而被污染,或者該人污染及毀壞其他人。此二詞(惡意與瞋恨)是怒氣的名稱。「昏沉」是心的疾病,「睡眠」則是心所的疾病;它們合稱為「昏沉與睡眠」。「覺知光明」:他具備清淨無蓋之想,無論白晝或黑夜都能覺知之前所見過的光明。「正念與正知」:他具備正念與智慧;提及這兩者是因為它們皆有助於覺知光明。他已經「超越懷疑」是說他已經跨越及超出了懷疑地過活。他「對善法毫無疑惑」,因為關於無可責備之法,他沒有懷疑:「這些是善的嗎?這些怎麼是善的呢?」這是簡短的解釋。關於這五蓋必須說的──詞源分析、相等等──這一切都已經在《清淨道論》裡說了。
74. 當比丘見到自己內心的五蓋還未棄除時,他將之視為負債、患病、被監禁、身為奴隸、荒野的道路
註:在此,世尊指出未棄除的貪欲蓋就像是負債,其餘諸蓋則像是患病等等。其類似性如下。
對於向別人貸款之後把它揮霍掉的人,當他們(債主)叫他還債,對他粗言惡語,綁他及打他時,他都無法保衛自己,必須忍受這一切,而其債務即是他必須忍受它們的原因。同樣地,若人對他人生起了欲念,以〔那人〕為貪相應心的目標,當那人對他粗言惡語,綁他及打他時,他都必須忍受這一切,而其貪欲即是他必須忍受他們的原因。其中一個例子即是被一家之主〔她們的家公家婆〕打的女人〔,而她們的貪欲即是她們必須忍受它的原因〕。如是,當視貪欲為債務。
對於患了膽汁病的人,如果給他蜜糖或糖等東西,他會由於自己的膽汁病而不能品嚐它們的美味。他會以為它們是苦的,而把它們吐出來。同樣地,對於充滿瞋恨之人,即使他那慈悲的戒師或導師只是輕微地訓誡他,他也無法接受訓誡。他會排斥它,說道:「你太過壓迫我了!」然後離去〔,不是四處遊蕩,就是還俗〕。就好像患上膽汁病的人不能品嚐蜜糖或糖的美味一般,受到瞋恨征服的人無法品嚐佛陀教法之味,即禪那之樂等等。如是,當視瞋恨為疾病。
在節日時被關在監牢裡的人不能見到慶典的初、中、後。如果他於隔天被釋放出牢後聽到「啊,昨天的慶典多麼快樂!啊,有這麼美妙的舞蹈及歌曲!」時,他無法回答。為什麼呢?因為他自己並沒有享受到該慶典。同樣地,對於被昏沉與睡眠征服的比丘,當佛法開示正以各種方式進行著時,他無法明白它的初、中、後。於開示結束之後,當他聽到別人稱讚「啊,多麼好的佛法開示!有這麼好的辯論及譬喻!」時,他無法回答。為什麼呢?因為他受到昏沉與睡眠征服,而無法從該佛法開示獲益。如是,當視昏沉與睡眠為受囚於監牢之內。
對於一個奴隸,即使在節日慶典時玩樂,也可能被告知:「有某件緊急的任務要你去做。趕快去辦!如果你不去,我將斬掉你的雙手、雙腳、雙耳或鼻子!」因此他必須趕快去辦(那件事),不能享受慶典的初、中、後。為什麼呢?因為他必須服從他人。同樣地,當不精通戒律的人,為了隱居而去到森林裡時,他可能會犯了某個小罪,甚至會以為不受允許的肉為允許的。在那時候,他必須捨棄隱居。為什麼呢?因為他已被掉舉與追悔征服。如是,當視掉舉與追悔為作為奴隸。
有個人走在一條荒涼的道路上,知道那是盜賊打劫殺人的好機會,因此,甚至聽到樹枝搖動的聲音或鳥叫聲也都使他感到恐慌害怕,心想:「盜賊來了!」向前走〔了一小段〕,他就〔因為憂慮與害怕而〕停下來及轉回頭〔,心想:「誰知道走在這樣的荒野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停下來的地方多過他走的地方。他幾經辛苦地才到達安全之地,或者根本就到不了。同樣地,若人對八件事起疑,他將會繼續懷疑:「導師是否真的是佛陀?」而無法解決(自己的疑心),也無法充滿信心地接受他。由於做不到這一點,他不能達到聖道及聖果。因此,就好像走在荒涼道路上的旅人,由於懷疑是否有盜賊,而不斷地感到猶豫不決、驚慌及缺乏信心,為自己製造了達到安全處的障礙,同樣地,由於懷疑導師是否真的是佛陀,而不斷地感到猶豫不決、驚慌及缺乏信心,為自己製造了達到聖者之境的障礙。如是,當視懷疑為荒涼的道路。
新疏:(上述的)八件事記載於《分別論》之中:「其中,什麼是懷疑?有人懷疑且不信導師、佛法、僧團、(三)學、過去世、未來世、過去與未來世、緣起。」
75. 然而,當他見到內心的五蓋已被棄除,他視之為還清債務、健康無病、獲釋出獄、免為奴隸、安全之地。
註:在此,世尊指出棄除貪欲蓋就像是還清債務,棄除其餘諸蓋則像是健康無病等等。其類似性如下。
有人貸款做生意而有成就。他想:「債務是障礙的根源。」因此,他還清貸款及利息,然後把貸款單撕掉。從那一刻起,沒有人會再派使者或送信給他(提醒他的債務)。當見到(以前的)債主時,他可隨心所欲從座位起身或坐著不動。為什麼呢?因為他不再受他們牽制,不需再依靠他們。同樣地,比丘想:「貪欲是障礙的根源。」因此,他培育六種法及去除貪欲蓋。當如此去除貪欲之後,他不再對外在事物執著或貪染,就好像還清債務之人在見到(以前的)債主時都不會感到害怕或驚慌,同樣地,該比丘對外在的對象沒有執著或束縛。即使他見到天界的顏色,也不會有煩惱干擾他。因此,世尊說去除了貪欲就好像是還清了債務。
新疏:(為了去除貪欲蓋而)應當培育的六種法是:學習不淨相(那就是身體的可厭本質);致力於修行不淨觀;守護根門;飲食適量;親近善知識;適當的言論。
註:患上膽汁病的人以藥控制該病。從那一刻起,他得以享受蜜糖或糖等東西的美味。同樣地,比丘想:「瞋恨是危難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培育六種法及去除瞋恨蓋。當如此去除瞋恨之後,他會恭敬地接受關於行為等的戒條,依照它們訓練自己及喜歡它們,就好像已從膽汁病復原的人一般,能夠食用蜜糖或糖等東西,享受它們的美味。因此,世尊說去除了瞋恨就好像是健康良好。
新疏:(為了去除瞋恨蓋而)應當培育的六種法是:學習慈愛相;致力於修行慈愛禪;思惟自己所造之業是自己的財產;數數如理思惟;親近善知識;適當的言論。
註:有人在節日時被關在監牢裡。(出牢後)在以後的節日裡,他想:「由於自己疏忽,以前我被關在監牢裡,而沒得享受慶典。現在我應當謹慎。」所以他變得謹慎,以致他的敵人沒有機會(使他再被關在監牢裡)。在享受慶典之後,他愉快地歡呼:「啊,多麼愉快的慶典!啊,多麼愉快的慶典!」同樣地,比丘想:「昏沉與睡眠是危難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培育六種法及去除昏沉與睡眠蓋。當如此去除昏沉與睡眠之後,他得以享受法慶的初、中、後,而證悟阿羅漢果及四無礙解智(paṭisambhidāñāṇa),就好像從監牢中被釋放出來的人,甚至能夠享受慶典的初、中、後長達一星期。因此,世尊說去除了昏沉與睡眠就好像是被釋放出牢。
新疏:(為了去除昏沉睡眠蓋而)應當培育的六種法是:知道飲食過量是(導致昏沉與睡眠的)因素;轉換身體姿勢;作光明想;住在露天下;親近善知識;適當的言論。
註:通過朋友的協助,奴隸付錢給其主人,而獲得了自由身。從那一刻開始,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任何事。同樣地,比丘想:「掉舉與追悔是危難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培育六種法及去除掉舉與追悔蓋。當如此去除掉舉與追悔之後,他得以愉快地修行出離,而掉舉與追悔再也不能強硬地阻止他這麼做,就好像自由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任何事,而沒有人能夠強硬地阻止他這麼做。因此,世尊說去除了掉舉與追悔就好像是脫離奴隸的身份。
新疏:六種法是:多學;發問;精通戒律;與上座比丘相處;親近善知識;適當的言論。
註:在帶了自己的財物之後,強壯的人在眾隨從的陪伴之下,全面武力裝備地越過荒涼之地。眾盜賊甚至在很遠之處見到他們時即已逃走。在順利地跨越荒野,而到達安全之地時,他將會充滿喜悅。同樣地,比丘想:「疑是危難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培育六種法及去除疑蓋。當如此去除疑之後,他越渡了惡行之荒野,而到達至上的安全處,即不死的涅槃,就好像強壯的人在眾隨從的陪伴、全面武力裝備之下,感到無畏,視眾盜賊如草,順利地越過荒野,而到達安全之地。因此,世尊說去除了疑就好像是安全之地。
新疏:六種法是:多學;發問;精通戒律;勝解;親近善知識;適當的言論。
76. 當他見到內心的五蓋已被棄除時,內心就會生起愉快……
註:「生起愉快」:生起愉快的素質(tuṭṭhākāra)。「當他內心愉快時,喜悅就會生起」:對於愉快的人,喜悅就會生起,震動了他的全身。
「當他內心充滿喜悅時,身體就會變得輕安」:對於心與喜悅相應的人,他的名身變得輕安;它變得不受干擾。「會感到快樂」:他體驗身心的快樂。「他的心變得專注」:對於體驗這種出離樂的人,(他的)心透過近行及安止的方式而變得專注。
新疏:「愉快的素質」:透過這一點,論師顯示了未成熟的喜悅。由於還未成熟,在愉快階段的(喜悅)就只是愉快的素質而已。
「對於愉快的人」:註疏說:「對於透過達到繼起階段的喜悅而感到愉快的人。」在這種情況裡,「愉快」一詞可以理解為「繼起喜」(okkantikā pīti)。「喜悅就會生起,震動了他的全身」:註疏解釋這一句的含意,說道擁有遍滿的特徵之喜悅生起,透過它本身的遍滿性及透過產生殊勝的色法而震動了全身。在這種情況裡,「喜悅」一詞可以理解為「遍滿喜」(pharaṇā pīti)。在此,身體的震動是產生喜悅之流,喜悅遍滿了全身。
「名身」(nāmakāya):在此,這是指整堆的非色法,而不是指「身輕快性」(kāyalahutā)等詞所指(不包括識蘊在內)的受、想、行三名蘊,也不是指「身處」(kāyāyatana)等詞所指的色身。輕安是指兩種輕安(識的輕安及其他三名蘊的輕安)。「不受干擾」:不受煩惱干擾;這是指已經棄除掉舉等煩惱的干擾。」
「他體驗身心的快樂」:透過上述的遍作修習,他體驗心的快樂,並且由於他的身體被該(心的快樂)所產生的殊勝色法遍滿了,他也體驗身體的快樂。
這種「出離樂」(nekkhammasukha):近行定之樂稱為出離是因為它已經脫離了煩惱與諸蓋,安止定之樂稱為出離則是因為它屬於初禪。由於定力以這兩種方式產生,所以說:「透過近行及安止的方式。」
在此,這是它的要旨。從去除貪欲至身輕安者體驗樂的階段是禪修的遍作修習(預作修習),而不是安止。但「體驗樂者的心變得專注」則包括遍作定及安止定兩者,因為樂是安止的原因,也是近行修習的原因,也因為初禪等安止是通過因果關係而達到的。或者,跟遍作樂一樣,安止樂也是安止定的原因;如是,護法論師接受安止樂為安止定的其中一個原因。
禪那
77. 他遠離感官欲樂,遠離不善法,進入並安住於……初禪
註:提及這一點是為了顯示當心因近行定而變得專注時的更高層次成就,也為了顯示當心因安止定而變得專注時的定力分界。
新疏:上一節經文的尾端提到「由於快樂,他的心變得專注。」這指出透過近行及安止兩種方式令心專注。在這種情況裡,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始於『他遠離感官欲樂』等的教法有什麼目的?」論師給予上述的話作為回答。
「為了顯示更高層次的成就」:那就是為了顯示將會證得的成就:高過近行定的初禪等等;高過初禪的第二禪等等。因為初禪等這些成就必須透過先成就近行定才能達到,沒有近行定的話就不能達到,而且順序地發生的愉快等各種原因也是成就第二禪的必備條件。
「為了顯示定力的分界」:這是有關以概括性的詞語「由於快樂,他的心變得專注」來形容的安止定──為了顯示把它歸納為第二禪等等及第一種神通等的分析。
他以由遠離而生的喜樂灌注、滲透、浸泡、充滿他的全身
註:「他灌注」:他滋潤;他把喜樂擴展至每一處。「滲透」:他塗滿一切處。「浸泡」:猶如把風箱注滿空氣一般,他(把身體給)注滿了。「充滿」:他遍滿一切處。「他的全身」:由四界組成的色身。
「他的身體沒有任何部份」:這比丘身體的每一部份,在業生色流產生的地方,沒有任何部份,甚至是皮膚、肌肉或血液的一小部份,是不被初禪之喜所充滿的。
對於第二禪的譬喻,色身好比是湖,第二禪之樂則好比是湖水。
新疏:對於第三禪的譬喻,色身好比是蓮花,第三禪之樂則好比是湖水。
註:對於第四禪的譬喻,提及白布是為了顯示充滿熱能。因為骯髒的布不充滿熱能,剛洗乾淨的布則充滿強烈的熱能。在這譬喻裡,色身好比是布,第四禪之樂好比是充滿熱能。因此,就好像一個剛洗好澡的男人,以一塊乾淨的布從頭蓋滿全身地坐著,其身體的熱能擴散至整塊布,沒有任何一部份的布是不被熱能所充滿的。同樣地,該比丘的色身沒有任何部份是不被第四禪之樂所充滿的。應當如此理解在此的含義。
新疏:問:在提到「其色身沒有任何部份是不被白布所充滿的」時,聖典是說身體被白布充滿,而不是說該布被熱能充滿,不是嗎?
答:預期著這個問題,論師說「在這譬喻裡」等等。意思是應當依(論師的)解釋來理解其含義,因為色身好比是布,第四禪之樂好比是充滿熱能。透過這一點,他顯示提及身體時應當理解它好比覆蓋著它的布塊,而提及該塊布時,應當理解它是指因為該布而充滿熱能;(否則)該譬喻就跟所要比照的對象沒有關連,而且身體是不可能被白布充滿的。
所舉出的這一個譬喻擁有「必須分析的含義」(neyyatthato),因為世尊的教法是多樣化的。應當把禪修者的色身視為相當於布塊,因為它將會被第四禪之樂充滿,就好比是被熱能充滿一樣。第四禪之樂好比充滿熱能,因為它充滿了禪修者好比布塊的色身。(在這個譬喻裡)該男人的身體就好比第四禪本身,因為禪那是樂的基礎,就好像(該男人的身體)是充滿熱能(的基礎)。於是論師說「因此」等等。因為這指出前文的正確性。在此,聖典裡說到「以清淨、光明的心」,世尊所提及的心是指第四禪之樂。為了顯示這一點,註釋提及第四禪之樂兩次。
問:但是在第四禪裡並沒有樂,只有舒適相(sātalakkhaṇa),不是嗎?
答:是的。然而,在此捨本身由於其寂靜性而被稱為「樂」。因此,《迷惑冰消》裡說:「由於其寂靜性,捨被稱為樂。」
註:對於四種禪那的次第解釋與修行方法,在《清淨道論》裡有記載。所以在此並不詳細地解釋它們。
不要以為這一個階段只是指出證得色禪者,而沒有針對證得無色禪者而言。因為沒有透過十四種御心法掌握八定是不可能證得任何神通的。在聖典裡只提及色禪,但是也應該解釋無色禪。
新疏:這麼說是因為八定是證得神通不可或缺的條件。十四種御心法是:一、順遍;二、逆遍;三、順逆遍;四、順禪;五、逆禪;六、順逆禪;七、跳禪;八、跳遍;九、跳禪與遍;十、超支;十一、超所緣;十二、超支與所緣;十三、支的確定;十四、所緣的確定。這些已經在《清淨道論》(第12章.第3-7節)裡解釋了。
即使已經掌握了各種禪那的五自在,即轉向等等(見《清淨道論》第4章.第131節),十四種御心法還是修證神通的主要條件。只是掌握了色禪,而沒有掌握無色禪是不能夠成功地證得(神通)的。因此無色禪是證得神通不可或缺的條件。
問:如果無色禪應該被包括在經文中,為什麼世尊省略了它們不說?
答:因為色界的第四禪是一切神通的特別基礎。因為即使(無色禪)是證得各種神通不可或缺的條件,後者以色界的第四禪為它們的特別基礎。因此,為了顯示第四禪是它們的基礎,所開示的教法停於該處(第四禪)。但這並不是說無色禪是不必要的。因此論師說:「但是也應該解釋無色禪。」
觀智(vipassanāñāṇa)
85.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光明、無垢、無瑕、柔軟、適業、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
註:他顯示該比丘已經透過十四種御心法掌握八定。其餘的應當依照《清淨道論》(第12章.第13-19節)裡所解釋的來理解。
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智見
註:在此,「智見」(ñāṇadassana)可以是指道智、果智、一切知智、省察智或觀智。在「賢友,什麼是為了智見清淨才跟隨世尊而過的梵行生活?」這一句經文(《中部》24)裡,道智被稱為「智見」。在「這是另一個過人之境、聖者的智見成就、已獲得的舒適住處。」這一句經文(《中部》31)裡,智見是果智。在「當時智見在世尊(的心中)生起,(了知)阿拉拉加拉麻(Ālāra Kālāma)已在七天前去世了。」這一句經文(《中部》26)裡,它是一切知智。在「智見在我(心中)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我的最後一生。』」這一句經文(《中部》26)裡,它是省察智。然而,在此,當說到「他使心傾向於智見」時,稱為「智見」的是觀智。
「他使心傾向」:他使自己的心傾斜、滑向、斜向於產生觀智。
這是我的身體,擁有色身,由四大所組成,源自父親與母親,依靠飯與粥來增進它、它是無常的、會受到觸痛與壓迫、會解體與分散
註:它是無常的,因為在存在之後,它不復存在。它會受到觸痛,因為它被塗上(香水等),以便去除臭味。它會受到壓迫,因為它被按摩,以便去除肢體的不適,而且當小孩子擁有由於在胎內(受到擠壓而)變得畸形的肢體,在嬰兒時期,他們被擺放躺在兩腿之間,以及被拉扯、推壓,以便他們的肢體恢復正常的形狀。它會解體與分散,因為雖然獲得如此保養,它的本質就是要分解四散。其中六詞表示生起,最後二詞與無常則表示壞滅。
新疏:(經中的)這九個詞顯示觀照身體必須遭受生起與壞滅。表示生起的六個詞是:擁有色身、由四大所組成、源自父親與母親、依靠飯與粥來增進它、會受到觸痛、會受到壓迫。
問:坦白說,說中間三個詞表示生起是正確的,因為它們傳達了那樣的含義。但是怎麼能夠說沒有傳達該含義的「擁有色身、會受到觸痛、會受到壓迫」這些詞句表示生起是正確的?
答:是正確的,因為它們的確傳達了那樣的含義。「擁有色身」一詞傳達「具有色身」的含義,因為色身包括作為自己的緣的火界與食素。「會受到觸痛、會受到壓迫」這兩個詞則傳達了「透過產生適當的色身而獲得正常形狀」的含義。
而這是我的心,依靠色身支持,並且緊繫於色身
註:心依靠且緊繫於由四大組成的身體。
新疏:這麼說是因為「觀心」(vipassanācitta)依靠包括在色身之內的心所依處的支持。因為只有當時發生的觀心立刻被直接識知為:「這是我的心。」它緊繫於色身,因為它不能脫離色身地生起,也因為它緣取稱為「色身」的色法為目標。
86. 註:應當如下地理解寶石譬喻的用法。寶石好比色身,穿過其中的線好比觀智。視力敏銳的人好比證得觀智的比丘。該人把寶石拿在手中,檢察它,而且清楚地了知「這是一顆寶石」的時刻,就好比該比丘把心傾向於觀智之後坐下,清晰地了知由四大組成的色身。該人清楚地了知「有一條線穿過其中」的時刻,就好比該比丘把心傾向於觀智之後坐下,清晰地了知觸五法,或一切心與心所法,或只是觀智,緣取它為目標。
新疏:「緣取它為目標」(tadārammaṇānaṁ):它們緣取稱為「色身」的色法為目標。透過提及觸五法及一切心與心所法,觀心的各種法也已經包括在內。
問:那麼為什麼提到觀心本身?
答:因為「而這是我的心,依靠色身支持,並且緊繫於色身」這一句經文可以只是指觀心而已。因為在以觀智了知「這是我的身體」之後,他如此觀照它為(觀心)的助緣與目標:「就是這與觀智相應的心依靠色身支持,並且緊繫於色身。」所以在此可以只說觀心而已,而不提及別法。因此論師說:「或只是觀心。」
在此提及「觸五法」是因為《法聚論》(Dhammasangaṇī)等裡的教法明顯地指出這一點。「一切心與心所法」:為了毫無遺漏地包含一切相關之法。「觀心」:因為根據辭句的教法,它是主要的因素。
註:這觀智就在聖道之前生起,雖然如此,在這裡提及它是因為一旦開始解釋神通就沒有空間來解釋它。在這裡提及它也是為了幫助已證得神通者去除恐懼。因為在人們透過天耳智聽到恐怖的聲音,或透過宿命智憶起可怖的諸蘊,或透過天眼智看見恐怖的形象時,如果不曾觀照(諸行)為無常等,恐懼與驚悸就會產生,但是如果他曾經觀照(諸行)為無常等,它們就不會產生。再者,在這裡提及它是因為觀智之樂是個別的沙門果,導致獲得聖道與聖果之樂。
新疏:可能會有批評說既然觀智就在聖道之前生起,那麼就應該在五種世間神通之後、但在第六種神通之前提起它。如此,為什麼在所有的神通之前提起它?(在此)舉出依照註釋的解釋來解除該批評。
「沒有空間來解釋它」:在解釋五種世間神通之後,就必須緊接著解釋第六種神通,就好像在無數經裡的作法,因為它擁有神通的特徵,因此被歸納在(神通)這一類別。但是不能把觀智插在世間神通與第六種神通之間來解釋,因為它缺少神通的特徵,因此不能歸納在(神通)這一類別。因此在諸神通之間沒有空間可提供給觀智。因為沒有機會在該處解釋它,所以在這裡解釋觀智,也就是在色界的第四禪之後。
「透過天眼智看見恐怖的形象」:在此也可以把它說成「當他以肉眼看見他以神變智變化出來的可怖形象時……。」因為恐懼與驚悸能夠產生於已證得神通、但還沒有徹知根本的人,就好像住在烏迦瓦里卡(Uccavālika)的大龍長老(Mahānāga Thera)。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以肉耳聽見自己以神變智變化出來的可怖聲音,也就好像大龍長老的例子。因為該長老(以神變智)變化出怒奔而來的純白雄象,而當他看見該象及聽見牠的聲音時,恐懼與驚悸在他心中生起。
意生身智(manomayiddhiñāṇa)
87. 他變出另一個具足色法、由心意所生、一切器官俱全、諸根完整無缺的身體
註:「意生」(manomaya):由心所造。「諸根完整無缺」:在形態上沒有缺少任何根。因為如果擁有神變智者白,他變化出來的形象也是白的。如果他的耳朵沒有穿洞,該形象也擁有沒有穿洞的耳朵。因此它在每一方面都跟他相同。
新疏:「在形態(saṇṭhāna)上沒有缺少任何根」:在形態上它眼、耳等俱全。因為所變化出來的形象(對感官目標)不敏感。這一句顯示該形象也沒有命根等等。「在形態上」:就好像蓮花瓣只是在形態上相似而已,而不是在根門上(與眼睛)一樣擁有領受色塵的能力。
88. 註:舉出三個譬喻來顯示(意生身及其原身的)類似性。因為在莢裡的蘆葦跟其莢類似;劍跟其鞘類似,因為他們把圓形的劍裝在圓形的劍鞘裡,把扁平的劍裝在扁平的劍鞘裡;蛇的蛻皮跟蛇類似。雖然經文上說「假設有人將蛇從牠的蛻皮中拉出來」,就好像他親自用手把牠拉出來,我們應該明白他是用心想像把牠拉出來,因為沒有人能夠把蛇從牠的蛻皮中拉出來。蛇透過四種方法自己捨棄蛻皮:透過遵從其類的規則;透過木桐或樹來幫助自己;透過自己的力量,那就是把自己從蛻皮中拉出來的力量;透過對舊皮感到厭惡,就好像它在吞噬自己的身體。如是,應當理解經文是指用心想像把蛇拉出來。
應當如下地理解這裡的譬喻用法:比丘的身體好比是莢等,所變化出來的形象則好比是蘆葦等。然而,在此的變化方法,以及接下來的神變智等五種神通,已經在《清淨道論》(第12-13章)裡詳細解釋了。所以應當依照在那裡所述的方法來理解它們;在此只多加了譬喻。
神變智等等(iddhividhañāṇādi)
90. 註:其中,善巧的陶藝家等好比證得神變智的比丘;調製好的黏土等好比神變智;塑造他想塑造的器皿好比該比丘(透過神變智)的變化。
92. 註:由於荒涼的道路可怕且危險,憂懼、驚恐的人無法分辨定音鼓與小鼓的聲音。在天耳智的譬喻裡,佛陀沒有提荒涼的道路,但是「大路」一詞表示安全之路。因為當人悠閒地走在安全無險的道路上,用一塊布蓋好頭(來擋風與防太陽曬),他能夠輕易地分辨上述的聲音。聽到的聲音對他變得清晰的時候好比遠近的天界與人間的聲音對禪修者變得清晰的時候。
94. 在他心智的譬喻裡,就好像當少男檢察自己的臉部映像時,臉上的痣對他變得清晰,同樣地,對於坐著使心傾向於他心智來涵蓋別人的心的比丘,別人的十六種心變得清晰。
96. 在宿命智的譬喻裡,只提及在同一天去過的三座村莊,因為就是在同一天裡所做的事才明顯。其中,那個去過三座村莊的人好比證得宿命智者,三座村莊則好比三世。就好像在同一天裡所做的事對該人來說很明顯,在那三世裡所做的事對於坐著使心傾向於宿命智的比丘來說也同樣的明顯。
98. 在天眼智的譬喻裡,位於中央廣場具有樓上陽台的建築物好比比丘的色身,站在陽台上的視力敏銳的人則好比證得天眼智的比丘。進入屋子的人好比以結生(心)投進母胎的人;離開屋子的人好比從胎中出來的人;在街上行走的人好比〔在生死輪迴裡〕不斷地輪迴的人;坐在中央廣場上的人好比在三界各處投生的眾生。這些人對站在建築物陽台上的人呈現得明顯的時刻──這就好比眾生在三界各處投生對於坐著使心傾向於天眼智的比丘呈現得明顯的時刻。這麼說是為了方便教學,事實上無色界不在天眼智的範圍之內。
新疏:「為了方便教學」:只為了方便教學,不是因為投生在無色界的眾生可透過天眼智清楚地看到。因為如果說「除了無色界」或「在二界裡」,該教法就不易理解。
漏盡智(āsavakkhayañāṇa)
99. 當他的心如此專注……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於漏盡智
註:「當他的心如此專注」:在此,應當理解第四禪之心作為觀智的基礎。
新疏:根據培育觀智的人,觀智可分為三種:大菩薩的觀智、辟支菩薩的觀智、聲聞菩薩的觀智。對於大菩薩及辟支菩薩,觀智是從「思所成智」(cintāmayañāṇa)開展出來、無師自通的觀智。對於聲聞弟子,其觀智源自他人的指導,是從「聞所成智」(sutamayañāṇa)開展出來的。《清淨道論》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詳細地解釋後者,在以下的文段裡等等顯示它的多樣化:「他應當從任何一個色界禪或無色界禪出定,除了非想非非想處之外。」再者,依無色(禪)的標題,以及依記載於四界分別(一篇裡)觀照諸界的幾個標題的任何一個,它是多樣化的。
然而,大菩薩的觀智涉及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歸納於二十四萬億個標題分類。這觀智完全成熟時產生作為聖道的基礎的遍作智,而聖道則是(佛陀成就)一切知智的助緣。諸註釋稱它(一切知智)為「大金剛智」(mahāvajira- ñāṇa),它極其深奧、非常微妙、不與他人共有。導師的二十四萬億每天例常禪定被稱為進入以作為觀智的基礎,根據其發生方式的分析而分類為二十四萬億種。護法論師(Ācariya Dhammapāla)在其註解《清淨道論》的《勝義燈註》(Paramatthamañjusā)概略地講述佛陀的觀智的進展。有興趣的人應該參考該著作。在此(經中)要講的只是聲聞弟子的觀智。
註:「他引導其心,使心傾向」:他使自己的觀心傾斜、滑向、斜向那個方向。
「於漏盡智」:為了產生漏盡智。在此,道、果、涅槃與壞滅稱為漏盡(āsavakkhaya)。在「滅盡智、無生智」這句經文裡(《長部》33),道稱為漏盡。在「透過滅盡諸漏,他是沙門」這句經文裡(《中部》40),漏盡是果。在「常挑他人的過失及貶低他人者,其漏增長。滅盡諸漏離他真是遙遠。」(《法句經》第253首偈)這句經文裡,漏盡是涅槃。在「諸漏之滅盡,它們的離去、分解、無常及消失」(出處還未找到),漏盡是壞滅(bhanga)。在此所指的是涅槃;說是指阿羅漢道也適當。
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
註:他如此透過通達其精華特相而如實地了知整個苦聖諦:「就只有這麼多苦,超越此就沒有苦。」他如此透過通達其精華特相而如實地了知產生該苦的貪愛:「這是苦的原因。」(了知)證悟之後會導致苦及其因滅盡、不再發生之法,(即)涅槃:「這是苦的滅盡。」以及(了知)導致證悟的聖道:「這是導向苦滅之道。」
新疏:「透過通達其精華特相」(sarasalakkhaṇa-
paṭivedha):論師顯示「如實」了知是指透過通達精華特相來了知。精華(rasa)是自性(sabhāva),應當被「品嚐」或了知。某法自己的精華是它的特別精華(sarasa),它本身就是相。因此(上述的片語)是指:透過無痴地通達該(相)。而(關於第一聖諦)「透過無痴地通達該(相)」是指智慧產生之後不會有愚痴障礙確定苦諦的特徵(sarūpa)等等。所以說:「他如實了知它。」
當聖典說「這是苦」以顯示比丘透過確定、徹知直接識知苦聖諦而掌握了它時,論師說:「就只有這麼多苦,超越此就沒有苦。」透過第一個片語,他顯示在確定之後已經掌握了它,而透過第二個片語顯示在徹知之後已經掌握了它。所以說:「整個苦聖諦。」貪愛被稱為「苦的原因」,因為苦緣於它而產生。
「證悟之後會導致苦及其因滅盡、不再發生之法,(即)涅槃」:這是說(它們)依靠涅槃(而滅盡);涅槃是聖道(生起)的其中一個原因,作為聖道的所緣緣。涅槃被稱為「它們不再發生」,因為由於它(etena),它們不再發生,所以涅槃是它們不再發生的原因(nimitta),或者是因為它是它們不再發生之境(ṭhāna),意思是它們不在該處(ettha)發生。
他如實地了知:「這些是諸漏。」
註:依特徵顯示諸聖諦之後,佛陀在接下來的經文裡說到諸漏,以便依煩惱再次比喻性地解釋它們。
新疏:「依煩惱」:這就是說依照組成諸漏的煩惱。採用「比喻性地」(pariyāyato)一詞是因為諸漏是苦諦的比喻性(pariyāya)表達方式,事實上它們包括在它(苦諦)之內,而它們的原因、滅盡及導致它們滅盡之道則各自是其餘(三)聖諦比喻性表達方式。在此只提及諸漏〔而沒有提及其他煩惱〕,因為該段經文提到漏盡智〔而沒有提及其他煩惱滅盡〕。因此,當說到「他的心從欲漏、有漏、無明漏當中解脫出來」時,解脫諸漏表達了解脫一切煩惱。
如此知見
註:佛陀解釋已經達到頂點之道及觀智。
新疏:由於說「他如實地了知:『這是苦。』」等等,在此所解釋的是混合道,因為出世間道和世間的觀智混合在一起(解釋)。
他的心從欲漏、有漏、無明漏當中解脫出來。心解脫之後,如此的智慧就會生起:「心已經解脫。」
註:透過「他的心(從……)解脫出來」這一片語,佛陀指出道心的剎那,透過「心解脫之後」這一片語指出果心的剎那,以及透過「如此的智慧就會生起:『心已經解脫。』」這一片語指出省察智的剎那。透過「生已滅盡」等經文,他指出省察智之境,因為當漏盡者以該智省察(自己的成就)時,他了知「生已滅盡」等等。
新疏:透過「如此知見」這一片語指出了(四種)突破的三種──遍知、現證與修習。然而,剩下的「捨斷突破」則透過「他的心(從……)解脫出來」這一片語指出來。因此論師說:「佛陀(以此)指出道心的剎那。」因為這四項任務透過了知四聖諦完成。
與註釋不同的另一種解釋是:「由於知,由於見,他的心從諸漏當中解脫出來。」在此,雖然知見的運作與解脫的過程同時發生,緣法與緣生法(之間的差別)依舊存在於同時發生之法。
在此,提到有漏時,見漏及欲漏已包括在內。所以當視見漏已包括在內。
他了知:「生已滅盡,梵行已立,應作皆辦,不受後有。」
註:問:他的什麼生已滅盡?他又如何了知這一點?所滅盡的不是過去生,因為那在以前已經滅盡了。它也不是未來生,因為沒有未來的精進。它也不是今生,因為它目前還存在。
答:那是如果沒有圓滿地培育聖道才有的生,由一蘊、四蘊或五蘊組成,各別屬於一蘊界、四蘊界或五蘊界。透過圓滿地培育聖道,該生已滅盡,因為它變得不可能在未來生起。省察了培育聖道所捨斷的煩惱之後,他了知由於沒有煩惱,即使有造作,也不能在未來產生結生。因此他了知:「生已滅盡。」
新疏:「那不是過去生」:該比丘的過去生不是被所培育的聖道滅盡,因為在培育聖道之前,它已經透過壞滅而滅盡。「它不是未來生」:發問者這麼說的目的是為了找藉口來批評,泛指未來,而不是指特定的未來。意思是透過培育聖道根本就沒有精進去滅盡未來(之法),因為精進只發生於當下存在之法,並不發生於當下不存在之法。然而,在此(佛陀的話)是指特定的未來,精進即運用於滅盡該未來。因此論師說:「那是如果沒有圓滿地培育聖道才有的生」等等。這點顯示事實上滅盡是與未來生(有關),透過培育聖道滅盡了作為它(未來生)的原因的煩惱。
註:「梵行已立」:已經圓滿地活出了聖道梵行。因為七種學者及善凡夫被稱為正在過著梵行生活,漏盡者則被稱為已經過著梵行生活。因此,省察自己的梵行生活,他了知:「梵行已立。」
「應作皆辦」:已經透過培育四道達到遍知、捨斷、現證及修習四聖諦而完成了十六項任務。意思是應當被每一道捨斷的煩惱已經被捨斷,苦的根已經被滅盡了。因為善凡夫等正在作應當作的;漏盡者已經作了應當作的。因此,省察自己以前應當作的,他了知:「應作皆辦。」
「不受後有」(nāparaṁ itthattāya):他了知:「現在已經沒有培育聖道的任務給我實行,以便達到此境,即以便(完成)十六項任務或以便滅盡煩惱。」或者,「此」可理解為「超越此」。所以他了知:「超越此現有如此發生的諸蘊相續流,我不再有接下來的諸蘊相續流。這些五蘊已被徹知,猶如已被根斷的樹。最後一個心識壞滅之後,他們(阿羅漢)將會猶如無油之火熄滅一般,達到無法形容之境。」
新疏:「以便(完成)十六項任務」:這是指聖道的遍知等作用。當人省察聖道時,這些透過道的力量變得明顯,所以在省察聖道之後,就很容易省察這些作用。如此透過四聖道的每一道的四項任務概括地說明了十六項任務之後,由於捨斷是它們當中的主要任務,也由於其他(任務)以這個為它們的目的,為了個別地說明它,論師說:「或以便滅盡煩惱。」
在第二種解釋裡,「超越此」擁有奪格的含義。「接下來」是指「未來」。組成最後一個個體的「這些五蘊已被徹知」,這就是說在被聖道確定之後,它們已被了知。以此他顯示它們沒有立足處(appatiṭṭhatā)。因為以沒有遍知為根基的那些(蘊)擁有立足處。正如所說的:「諸比丘,若有對色食的貪欲,取樂於它(色食),渴愛它,識從它獲得立足處而萌芽。」(《相應部》XII.64/ii.101)為了以譬喻闡明這一點,他說:「猶如已被根斷的樹。」猶如已被根斷的樹沒有根而沒有立足處,沒有支撐處,已被徹知的這些五蘊也是如此。
「無法形容之境」(apaṇṇattikabhāva):形容是透過以各種方式歸因當下存在的諸蘊而作出來。(說)他們「達到無法形容之境」是因為當如此的(諸蘊)不存在時,就沒有可以運用於它們的形容。
100. 大王,假設在山谷中……
註:視力敏銳的人站在湖邊可以清楚地看見蠔貝等的時刻,就好比坐著使心傾向於漏盡智的比丘清楚地了知四聖諦的時刻。
至此已解釋了十種智:觀智、意生身智、神變智、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透過天眼智成就的未來分智及依業投生智這一對智、天眼智(本身)、漏盡智。也應當知道對它們的目標的分析。其中,觀智有七種目標:有限與廣大;過去、未來與現在;內在與外在。意生身智只取(心)所造的色處為目標,因此其目標是有限、現在與外在。漏盡智所取的目標無量、外在與無法(依時間)形容。對於其餘的(智),它們的目標的分別已經在《清淨道論》(第13章.第102-129節)裡解釋了。
新疏:由於未來分智及依業投生智這一對智沒有記載於經文之中,它們被稱為「透過天眼智成就」。它的意思是,由於它們是透過天眼智成就,在提及後者時,這兩種智也間接地被包括在內,因為這兩種智是天眼智的分支。(在經文中)天眼智被稱為「死亡與再生智」。
大王,再也沒有比這種更殊勝與崇高的其他沙門果了
註:世尊結束他的教法於其巔峰阿羅漢果,說道:「再也沒有在任何方面比這種更殊勝的沙門果了。」
新疏:他結束他的沙門果教法。此教法不與他人共有,顯示外道導師的見解無內涵,去除詭詐、暗示等各種邪命方法,受到三種戒律莊嚴,解釋至上消除自我的修行,受到禪那與神通等過人法莊嚴,也受到十四種大沙門果莊嚴。猶如寶屋(裡的珍寶)最上等的是羽冠寶,因此他結束他的教法於其巔峰阿羅漢果,因為「解脫」這一詞表示已經教導了阿羅漢果。
阿闍世王自誓為在家弟子 回首頁
101.
註:細心聆聽了該開示的初、中、後,處處讚歎之下,國王想:「我已經問普通沙門與婆羅門這些問題很久了,但就好像打穀糠一樣,我沒有得到任何有實質的東西。啊,世尊具備如此殊勝的特質!他放大光明地回答我這些問題,就好像是為我點燃了一千盞燈。我已經被欺騙了很久,不知道佛陀殊勝特質的精神力量!」當他如此思惟佛陀的殊勝特質時,他的身體被五種喜遍滿了。表露自己的信心,他宣佈自己為在家弟子。為了指出這一點,所以有始於「世尊說完之後」的經文。
太美妙了,尊者!太美妙了,尊者!
註:在此用「太美妙了」(abhikkanta)這一詞來作為隨喜的表達方式。聰明的人在害怕、發怒、讚歎、激動、驚訝、歡笑、憂傷與自信的時刻會重覆某些詞句。在此,應當理解該重覆的宣言是由於自信與讚歎而說。或者,「太美妙了」是指極其優美、極其可欲、極其可喜、極其善。
在此,第一次宣說「太美妙了」時,該國王是在讚歎該教法,另一次則是表示其自信。這是其要意:「尊者,世尊的教法實在太美妙了。我依靠世尊的教法的自信實在太美妙了。」
或者他是在讚歎世尊的話本身,指出在每一種情況裡都有雙重含義。所以該聲明可以如此分析:「世尊之言實在太美妙了,因為它滅除過錯,幫助成就優越的特質。同樣地,(它雙重地美妙)因為它激發信心與智慧,因為它含有義理且辭藻妥善,因為它用詞易明但含義深奧,因為它悅耳且深得人心,因為它不自誇自擂也不貶低他人,因為它受到悲憫清涼且受到智慧清淨,因為它好聽又經得起考驗,因為它聽聞時愉快、分析時有益」等等。
國王接著以四個譬喻來讚歎該教法。這是其要義的分析:「就像將翻覆之物翻轉復正,同樣地,當我被翻覆至遠離正法、墮入惡法時,世尊幫助我脫離該惡法。就像使隱匿之物揭示顯露,同樣地,世尊揭示顯露教法,從迦葉佛的教化期消滅後就一直被邪見之林隱藏起來的教法。就像為迷路之人指示正途,同樣地,當我誤入歧途邪道時,世尊為我指出通向天界與解脫的道路。就像為黑暗中之人擎舉明燈,同樣地,在我沉入愚痴之黑暗當中、不能見到猶如寶石形狀般的佛法僧時,世尊為我帶來教法之燈,驅除了覆蓋那些形狀的愚痴之黑暗。由於世尊以這些方式為我開顯正法,(我說:)「世尊以種種方式宣說佛法。」
我歸依世尊、歸依法、歸依比丘僧團
註:如此讚歎教法之後,(為了)表達他對三寶的信心,他說「我歸依世尊」等等。意思是:「世尊是我的歸依處、我的至上依靠處、滅除痛苦者、提供幸福者。以此意願,我歸依世尊,我投誠他,我跟隨他,我服侍他。」或者:「我如此知道與了解(他)。」給予這最後一項解釋是因為(在巴利文的)詞根擁有「去」(gati)的含義,也擁有「了解」(buddhi)的含義。所以說「我去」也可以意指「我知道,我了解」。
「法」(Dhamma)這一個字源自動詞「支持」(dhāreti),因為它支持那些已經證道、證悟滅盡、依指導修行的人,防止他們墮入四惡道。在象徵上,法是聖道與涅槃。因為曾經這麼說:「諸比丘,在有為法(dhammā)的範圍裡,八聖道分是它們之中最好的。」(《增支部》4:34/ii.34)
法並不只是聖道與涅槃,而是也包括聖典之法及聖果。因為在「婆羅門青年華蓋(Chatta)的天宮故事」(《天宮事經》)裡說到:
離欲、無願又無憂、
無為法、優美、甜美、
使信服、分析得好──
我向此法尋歸依。
在此,「離欲」是道;「無願又無憂」是果;「無為法」是涅槃;「優美、甜美、使信服、分析得好」是分析為(經、律、論)三藏的諸法蘊。
僧團由那些透過見和及戒和團結的人組成。在象徵上,它是八種聖者的群體,因為在「華蓋的故事」裡說到:
那八種人見法者,
那四雙清淨的人,
施予他們果報大──
我向此僧尋歸依。
比丘僧團是比丘眾的僧團。對此國王宣佈自己的三歸依。
新疏:「透過見和及戒和團結」(diṭṭhisīlasanghātena):他們如此在見(方面)和合:「他(與梵行同伴)擁有聖潔、導向解脫、引導依它修行者至滅盡苦的相同見解地安住」(《中部》48),以及如此在戒(方面)和合:「他(與梵行同伴)擁有不破、不裂、無斑點、無雜色、解脫、智者讚歎、無著、對定力有益的相同戒律地安他」(《中部》48)。因此它的意思是:他們擁有相同的見與戒。因為無論聖者們住在哪裡,甚至有段距離,他們也透過他們殊勝特質之和諧達到和合。
前往歸依(saraṇagamana) 回首頁
為了通達有關歸依(的課題),應當理解以下解釋的方法:(一)歸依處(的含義);(二)歸依;(三)歸依者;(四)歸依之分析;(五)歸依之果;(六)污染;及(七)破除。
(一)關於歸依處(saraṇa)(的含義):它殺(hiṁsati),因此它是歸依處。意思是對於歸依者,它殺死與毀滅他們的怖畏、恐懼、苦與(投生)惡道的苦楚。「歸依處」是三寶的名稱。
或者,佛透過增長眾生的幸福及防止他們的危難,法透過使他們能夠越渡生命的荒野及給予他們安詳,僧則透過使得連他們最微小的宗教行為也會獲得許多的果報,而殺死了他們的怖畏。所以三寶也因此是歸依處。
(二)「歸依」是心的生起,此心透過對三寶產生信心與恭敬而沒有煩惱,視三寶為至上歸依處地生起。
新疏:「心的生起」(cittuppāda):歸依是與信、慧等其相應法聯合生起的心。它對三寶擁有如此的信心:「世尊圓滿覺悟,法已善說,僧團善修。」它也擁有對三寶的恭敬。透過該信心與恭敬,它「沒有煩惱」,也就是說它已經去除了疑、痴、無信等惡法。它視「三寶為至上歸依處」:三寶是它的至上歸依處、至上目標、保護與庇護所。
在此,透過提及「信心」,論師指明世間的歸依,因為受到信支配,而不是受到智支配;透過提及「恭敬」,他指明出世間的歸依,因為聖者透過對三寶殊勝特質的親證智而恭敬三寶。因此,透過這樣的信心,煩惱已經被替換地去除;透過這樣的恭敬,煩惱已經被根除不敬的原因地去除了。「視三寶為至上歸依處」是指以下所解釋的所有四種歸依。或者,信心與恭敬任何一詞皆可毫無差別地表示世間與出世間兩種歸依。因為提到信心可以是指不動搖的出世間信心及還會受到動搖的世間信心兩者。同樣地,提到恭敬也可以是指世間與出世間恭敬兩者。
註:(三)「歸依者」是具備該(心之生起)的有情。其意是以上述的心之生起來親近(三寶):「這三寶是我的歸依處,這是我的至上歸依處。」
(四)在「歸依之分析」裡,歸依有世間與出世間兩種。出世間歸依的成就發生於知見聖諦者在聖道的剎那;依其目標,它緣取涅槃為目標;以及依其作用,它對於整個三寶達到成就。
新疏:「它緣取涅槃為目標」:說到這一點時,它是指在象徵上成就四聖諦或道智本身是出世間歸依。因為在其中,在成就四聖諦時,歸依的污染已經被捨斷突破根除了。當透過現證突破徹知涅槃時,涅槃這一法成就了歸依;當透過修習突破徹知聖道時,聖道這一法成就了歸依。進入聲聞弟子(的智慧)範圍的佛陀之殊勝特質在被遍知突破徹知時成就了歸依。對於僧團之殊勝特質也是如此。所以他說:「它對於整個三寶達到成就。」
註:凡夫透過鎮伏歸依的污染而成就世間歸依;依其目標,它緣取佛法僧的殊勝特質為目標。在象徵上,它是對佛陀等激發信心的對象產生信心,而以信為根的正見則被稱為「見的正直」,是十種善業之道之一。
疏:「以信為根的正見」:在正見之前有上述的信,此信透過系統地以世間智慧知見世尊圓滿覺悟、法已善說、僧團善修而生起。以這一片語,論師指明世間歸依是具備上述特徵、以信為親依止的智慧。以「產生信心」這一片語,論師指出與智不相應的歸依,就像受到父母慫恿的小孩等情形。以「正見」這一詞,他指出與智相應的歸依。
註:世間歸依發生的方式有四種:透過奉獻自己、透過取三寶為自己的至上歸依處、透過接受弟子的身份、透過頂禮。
其中,「奉獻自己」是如此把自己獻給三寶:「從今天開始,我把自己奉獻給佛、法、僧。」「取三寶為自己的至上歸依處」是如此表達:「從今天開始,佛陀是我的至上歸依處,法是我的至上歸依處,僧團是我的至上歸依處。你可如此記住我。」「接受弟子的身份」是如此表達:「從今天開始,我是佛陀的弟子,是法的弟子,是僧團的弟子。你可如此記住我。」「頂禮」是對佛法僧最謙虛的素質,是如此表達:「從今天開始,我只對佛法僧三種歸依對象頂禮、恭敬起立、恭敬問訊及執行適當的任務。你可如此記住我。」歸依以這四種方式的任何一種進行。
再者,「奉獻自己」可以依以下的表達來理解:我把自己奉獻給佛、法、僧。我奉獻自己的生命給他們。我自己已經奉獻給了他們,我的生命已經奉獻給了他們。直至命終,我歸依佛陀。佛陀是我的歸依處、我的庇護所、我的保護所。」
「接受弟子的身份」可以透過大迦葉歸依的例子來理解,如下:「我將會見導師、世尊!我將會見阿羅漢、世尊!我將會見圓滿覺悟者、世尊!」(《相應部》16:11/ii.220)。
「取三寶為自己的至上歸依處」可以透過阿拉瓦加(夜叉)(Ālavaka)等歸依的例子來理解,如下:
我從村莊到村莊、
從城到城地遊行,
禮敬佛陀及其善說之法。(《經集》192)
「頂禮」可以如此闡明:「當時梵命(Brahmāyu)婆羅門從座位起身,整理上衣於一肩,以自己的頭頂禮世尊雙足,以口親吻世尊雙足,以自己雙手撫摸它們,以及說出自己的名字:『我是梵命婆羅門,尊敬的喬達摩!我是梵命婆羅門,尊敬的喬達摩!』」(《中部》91)
頂禮有四種:向親戚頂禮、因為害怕而頂禮、向老師頂禮及依據對宗教價值的尊敬而頂禮。在這四種當中,依據對宗教價值的尊敬而頂禮組成歸依,而不是其他(三種)。因為人們依至上而歸依,也只依至上而破除它。
因此,如果有一位釋迦族人或拘利族人頂禮佛陀,心想:「他是我們的親戚。」他並沒有因此而歸依。或者,若人由於害怕而頂禮佛陀,心想:「喬達摩沙門受到諸王禮拜,擁有極大的權力,如果我不頂禮他,他可能會傷害我。」(如此)他並沒有歸依。或者,若人憶及他向世尊以前還是菩薩的時候學習了某樣東西,或者向成佛之後的世尊學得某樣世俗的東西,而頂禮佛陀,心想:「他是我的老師。」(如此)他並沒有歸依。但若人頂禮佛陀時想:「他是世間上最值得(禮敬)者。」他即已經歸依。
反之,若一位已歸依的男或女在家信徒頂禮其他宗教的出家人,心想:「他是我的親戚。」他的歸依並沒有被破除,更別說是頂禮一位不是出家人的親戚。同樣地,若人由於害怕而頂禮國王,心想:「全國的人民都頂禮他,如果我不頂禮他,他可能會傷害我。」(如此)他的歸依並沒有被破除。若人頂禮自己曾經向他學習某種技藝的外道導師,心想:「他是我的老師。」他的歸依也沒有被破除。
歸依之分析應當如此理解。
(五)應當如下地理解「歸依之果」。在出世間歸依的情況裡(也就是聖道),四種沙門果是果報果,滅盡一切苦則是利益果。因為曾說到:
歸依佛法僧者,
以圓滿智慧知見四聖諦──
苦、苦集、苦滅及
導向苦滅的八聖道分。
這是平安的歸依處,
這是至上的歸依處。
依靠這歸依處,
他解脫一切苦。(《法句經》190-192)
再者,(世間)歸依的利益果可以依「不視任何有為法為常」等來理解。因為曾說到:「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已證得正見者視任何有為法為常、視任何有為法為樂、視任何法為我。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他會殺死母親、殺死父親、殺死阿羅漢、以瞋恨心導致如來流血、分裂僧團、指出(佛陀以外的)其他人為他的導師。這是不可能的。」(《中部》115)
世間歸依之果是(善)趣成就及財富成就。因為曾說到:
已歸依佛陀的人,
不會投生到惡道。
在捨棄人身之後,
他們填滿諸神群。(《相應部》4:37/i.27)
也有這麼說:「諸神之王帝釋天王及其八萬四千神眾去見目犍連尊者……目犍連尊者向他說:『諸神之王,歸依佛陀是好的。由於歸依佛陀,有一些在這裡的眾生在身體分解死亡之後,(投生)重現於善趣、天界。他們在十個方面超越其他神:天壽、天麗、天樂、天名、天權、天色、天聲、天香、天味與天觸。』」(《相應部》40:10/iv.275)對於歸依法及歸依僧也是如此。再者,歸依的殊勝果也可透過《維拉麻經》(Velāma Sutta)等來理解〔在這部經裡,佛陀說歸依的果報比最慷慨的布施的果報還要大(《增支部》9:20/iv.395)〕。
註:(六)關於「污染」,世間歸依受到對三種信仰對象(佛法僧)的無明、懷疑、誤解等污染,因此它不會很光明、遍滿。然而,出世間歸依則沒有污染。
(七)世間歸依的「破除」有兩種:當受指責與無可指責的。當受指責的在人奉獻自己等等給外道導師等的時候發生,這有不好的果。無可指責的在人死亡時發生,因為這不會產生業報,所以它沒有果。然而,出世間歸依則不會被破除。
應當如此理解歸依之污染與破除。
願世尊接受我為在家信徒
註:其意是:「願世尊如此接受我:『他是世家信徒』;願他如此記住我。」
在此,為了通達有關在家信徒的課題,應當理解以下各項:(一)誰是在家信徒?(二)為何稱他為「在家信徒」?(三)什麼是他的戒?(四)什麼是他的活命?(五)什麼是他的失敗?(六)什麼是他的成就?
(一)其中,誰是在家信徒?已經歸依的任何居士。所以曾說到:「大名(Mahānāma),當人已經歸依佛法僧,他於此是位在家信徒。」(《相應部》55:37/v.395)
(二)為何稱他為「在家信徒」(upāsaka)?因為他已經接近(upāsanato)三寶。因為他接近(upāsati)佛法僧,因此他是在家信徒。
(三)什麼是他的戒?五戒。正如所說:「大名,在在家信徒戒禁殺生、戒禁不予而取、戒禁邪淫、戒禁妄語、戒禁服食導致放逸的酒與麻醉品,他於此是位有戒行的在家信徒。」(《相應部》55:37/v.395)
(四)什麼是他的活命?捨棄五種邪命之後,他依法正命維生。因為曾說到:「諸比丘,在家信徒不可從事五種生意。是哪五種?武器買賣、人口買賣、供屠宰用牲畜的買賣、酒等麻醉物品的買賣、毒藥的買賣。這些是在家信徒不可從事的五種生意。」(《增支部》5:175/iii.206)
(五)什麼是他的失敗?失敗於戒律及活命,這是他的失敗。再者,使得他成為賤種、污穢及可厭的也是他的失敗。這是指五種素質,即沒有信心等。正如所說的:「諸比丘,擁有五種素質的在家信徒是賤種在家信徒、污穢的在家信徒、可厭的在家信徒。是哪五種?他沒有信心;他沒有戒行;他相信迷信的徵兆;他依靠徵兆,而不是依靠業;他尋求在此之外〔那就是在佛教之外〕的宗教師,而且先向該處示敬。」(《增支部》5:175/iii.206)
(六)什麼是他的成就?成就於戒律及活命,這是他的成就。同樣地,也有信心等五種素質使得他成為寶等等。正如所說的:「諸比丘,擁有五種素質的在家信徒是如寶在家信徒、如紅蓮華在家信徒、如白蓮華在家信徒。是哪五種?他有信心;他有戒行;他不相信迷信的徵兆;他依靠業,而不是依靠徵兆;他不尋求在此之外的宗教師,而且先向此處示敬。」(《增支部》5:175/iii.206)
我從今天開始終身歸依
註:「只要我的生命還存在,願世尊接受與記住我為侍者,為已經透過三歸依而歸依、不認任何其他人為導師的在家信徒。如果有人要以利劍砍斷我的頭,即使是如此,我也不會否定佛陀、法或僧團。」
尊者,罪惡戰勝了我
註:如此奉獻自己地歸依之後,國王這麼說,透露他所造的罪惡。
102. 大王,這就是在聖者的戒律中成長
註:「大王,這稱為在聖者的戒律中、在佛世尊的教化中成長。」什麼(是這)?見到自己的罪過為罪過,依法改正,以及在未來成就自制。
103. 他禮敬世尊,右繞三匝,然後離去
註:向世尊右繞三匝之後,他合掌於額頭示敬,面向世尊倒退,直到見不到世尊為止。世尊從視線消失之後,國王五體投地地頂禮,然後離去。
104. 諸比丘,這位國王毀了自己
註:意思是:「諸比丘,這位國王毀了自己、傷了自己、毀壞了自己的支助。他自己毀了自己,使得他沒有支助。」
新疏:透過毀了自己在過去世培育的善根、能夠在這一世帶來果報的善根,國王毀了自己。透過傷了那些善根,他傷了自己。以這兩個同義詞,佛陀指出他的惡行。為了指出透過毀壞其善根的支助而導致毀壞與傷害,所以說:「(他)毀壞了自己的支助。」「支助」(patiṭṭhā)與「根」擁有同一個含義;它稱為支助因為它支助沉入正性決定(也就是出世間道)。透過其惡行,他已經破壞與毀壞了自己所獲得的善助緣,如此他已經「毀壞了自己的支助」。由於他自己的善根支助已不復存在,國王「自己毀了自己」。
就在這一個座位上,他能夠生起無塵無垢的法眼
註:它「無塵」,因為它無貪欲塵等;它「無垢」,因為它無貪欲垢等。由於它是「見法之眼」(dhammesu cakkhuṁ),或由於它是「法造眼」(dhammamayaṁ cakkhuṁ),因此它是「法眼」。在其他地方,這是〔前〕三道的名稱,但在這裡只是指須陀洹道。
新疏:「見法之眼」:此眼是須陀洹道,這麼稱呼是因為它擁有「見」的含義;「法」是四聖諦之法,或是前三道之法。
「法造眼」:法產生之眼,那就是止觀之法。再者,由於「造」這個字的用法含有「由……構成」的含義,該巴利片語可以是指「由法構成之眼」,那就是由戒、定、慧這三法蘊構成。
註:這是(上述經文的)含義:「如果他沒有殺死他的父親,就在此時坐在這一個座位上,他能夠證得須陀洹道。然而,由於親近惡友〔提婆達多及其隨從〕,對他已形成障礙。雖然如此,他已親近如來及歸依三寶。因此,就像某個殺了人的人可以透過付罰款而被釋放,同樣地,透過我的教法的偉大,這位國王(來世)投生到銅鍋地獄裡,向下沉三萬年直達鍋底,再向上浮三萬年來到上面時,他就會被釋放。據說這是世尊所說的話,雖然它並沒有記載在經文之中。
新疏:「銅鍋地獄」:對於必須在此界體驗(痛苦)的眾生,一個大銅鍋將會由他們的業力產生。向下沉到鍋底、再向上浮到上面總共需要六萬年的時間。(投生到那裡的)其他眾生不斷地沉下浮上,在該處遭受折磨許多萬年。但這位國王並非如此。他將會如(上述)形容般沉下浮上一回而已,只遭受折磨六萬年,然後就會被釋放。
註:聽完這部經之後,國王是否有獲得任何利益?他獲得大利益。因為從他殺死父親的時候開始,無論白天或黑夜,他都不能夠睡覺。但自從他去見佛陀,聆聽這甜美有益的教法之後,他就能夠睡覺。他對三寶表示極大的恭敬。沒有人能夠比得上這國王所擁有的凡夫信心。而且在未來他將會成為辟支佛,名為勝利者(Vijita),然後達到般涅槃。
新疏:問:如果國王沒有被他的業障礙,在該座位上,法眼就會在他心中生起。那麼,他怎麼能夠在未來成為辟支佛,然後達到般涅槃?反之,如果他將成為辟支佛,然後達到般涅槃,怎麼說法眼原本能夠在他心中生起?聲聞菩提的親依止和辟支菩提的親依止不是不一樣的嗎?
答:這是沒有衝突的,因為他將會在這之後積累辟支菩提資糧。對於原本能夠透過聲聞菩提而證悟的眾生,如果在(兩個佛法教化期)之間的時期沒有機會證悟聲聞菩提,又如果他們發願(成為辟支佛),他們能夠透過辟支菩提而證悟。
然而,其他人說這位國王早已經發願要證得辟支菩提。因為即使眾生已經發過這樣的願,如果他們的終點還沒有固定(niyati),由於他們的智慧還沒有成熟,他們可能會在導師(佛陀)本人面前證悟聲聞菩提。因此世尊說:「諸比丘,如果這位國王沒有殺死他的父親」等等。
只有大菩薩(肯定會成佛的人)才不可能造(弒父、弒母等)五逆罪,而不是其他菩薩。因此,雖然提婆達多已經肯定會證悟辟支菩提,但還是瞋恨佛陀、世間的保護者,而造了更重的惡業。因此,由於業障,這位國王沒有得到「見(聖諦)之突破」的機會,但由於已經肯定會證悟辟支菩提,在未來他將會成為辟支佛,而達到般涅槃。
註:世尊如此說。諸比丘內心愉快,對世尊的話感到歡喜。
(沙門果經至此結束)